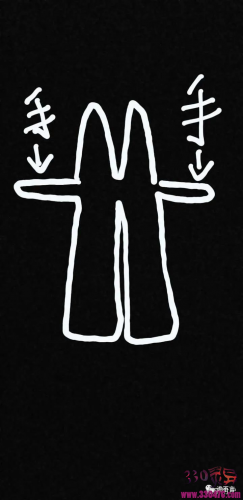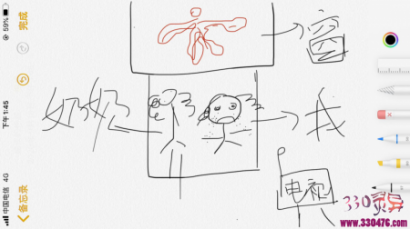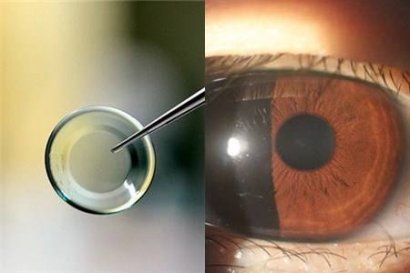忍不住也想把自己亲身经历亲耳听闻的一些奇闻趣事写下来,凑个数,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也当作工作之余的消遣。
我的老家在当地也算是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村庄,坐落于鲁中南丘陵地区。
村北是已经干涸的古雷泽湖,村南是一座以村庄命名的小山,据考证,此山另有名字,舜帝被继母赶出家后在此居住过,故又名妫停山。
紧靠村南边的是一条东西无限延伸的公路,村北有一条日夜不息的繁忙铁路通过。
小时候,村里各家各户一样穷,娱乐极其匮乏,收音机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大家的娱乐就是互相串门,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闲聊,各种各样古怪离奇的故事就在这种闲聊中不停的诞生,口耳相传,内容也不断变化、充实、丰富。
对我来说,最好的娱乐节目,就是听大人们聚在一起讲故事。
如今每次回到老家,都会听说曾经讲故事的人已逝,或者成为了故事中的人。
故事中的老家也不复原来的模样,有些伤感,有些惋惜。
把记忆中的故事记录下来,就当做对老家的一种怀念吧。
1、两个妇女这是与我有关的最早的一个故事,母亲给我说过无数次,但是算不得我的亲身经历。
母亲年轻的时候,有哮喘病,当地方言称之为齁包(含有嘲笑之意,嘴馋吃得太咸引起的咳嗽)。
我印象中的小时候,无论冬日夏天,母亲天天披着上衣坐在屋子里间(方言:堂屋内的套间)的床上,用被子围住半个身子,喉咙里发出吱吱的声音,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然后就是一阵阵剧烈的咳嗽。
旁边的窗台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褐色药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氨茶碱这种药,是家里的常备药。
窗台下,是一堆白色的硬纸壳针剂盒子。
那些空了的药瓶和针剂盒子也就成为了伴随我整个童年的玩具。
母亲说,一天,天刚黧黑(方言:傍晚),饭后她刚吃过药,坐在里间的床上喘得难受,也没看见门帘动,就看见两个妇女,都四五十岁,穿着白净布(方言:手工纺织的棉布,未加染色)的褂子,都包着白头巾,一个身材高点,一个身材矮点,走进了里间。
母亲问他们:“你们是谁?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两个妇女不理母亲,也不答话,径直走到床边就不见了。
母亲感到奇怪,还没眨眼的功夫,怎么就藏起来了?母亲赶紧从床上下来,床底下、柜子底下、装粮食的陶瓮后头,到处寻找,什么都没有找到。
母亲说,当时父亲就在外间,她问父亲,看没看见两个妇女进了咱家的里间?父亲说没看见人进来,什么都没看见,还说母亲看花了眼,说胡话。
据母亲说,从那时起,母亲就怀上了我。
有人说,那两个妇女是送子娘娘。
如果说是送子娘娘,我未免有些失望,不凤冠霞帔也就算了,至少也穿个像戏剧电影中的戏服,给人点“神仙”的感觉吧,我多次问母亲那两个妇女到底什么装扮,母亲说就是当年普通农村妇女的打扮。
后来我想,说不定是来投胎的呢,我认为母亲更有可能是看花了眼。
2、墙角的黑影应该还是学前,约五六岁。
初冬的晚上,月特别亮,高过树梢。
母亲让我去村里的供销社买顶针(一种做针线活的工具,戴在手指上的铁环),供销社在村子中间,离我家较远。
我买了顶针,顺便还买了两毛钱的散瓜子。
我吃着瓜子走到胡同口,看见一个不高的黑色影子站在胡同墙角,也就是我家的南墙与胡同西墙的夹角处,就像一个人低着头,靠着墙,在那一动不动地站着。
当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只是不想惊动那个黑影。
我蹑手蹑脚走到大门口,推开大门飞快地跑进屋里,给父亲和母亲说:“一个人站在咱家牛栏(方言:猪圈)墙外头。
”父亲和母亲本来正聊着天,他们听我一说,面面相觑,母亲说:“别胡说八道了,哪有人?”我拉着母亲的手说:“真有一个人,要不你去看看。
”母亲甩开我的手说:“小赊孩子(方言:当地骂自家孩子的常用口语。
绝对不可用来骂别人家抱养的孩子,大忌。
),别胡说。
”睡觉要锁大门,母亲不敢去,父亲也不敢去,推来推去,他俩作伴一起去锁了大门。
本来这事过去也就忘了,父亲和住在村北大池塘南岸的一位周姓的叔叔关系比较好,周姓叔叔的母亲是个神婆。
大约过了三四天,我跟着父亲去周姓叔叔家玩,我还清楚记得,在周姓叔叔家烤着火盆,周姓叔叔的母亲盘腿坐在她家正堂屋八仙方桌东侧的椅子上,喝了几碗茶,周姓叔叔的母亲突然来神了,打了个哈欠,开始下起神来。
周姓叔叔的母亲叫着父亲的小名说:“你这一段时间老是寻死上吊的,你阳寿还没尽来,那边不要你,你家老爷奶奶(方言:祖上)托我,叫我看着你,那天晚上,我在你家墙外头看着你来,叫孩子看见了,把孩子吓着了,你可别骂他,孩子没说瞎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父亲听得脸色煞白,拉着我要回家,周姓叔叔的母亲叫着父亲的小名又说:“你可别再寻死上吊的了,你阳寿还没到,回去给孩子他娘说,别骂他了,他没说瞎话。
”父亲回家给母亲一说,吓得他们很长时间晚上不敢出去串门。
3、房梁上的手记不清什么季节,也记不清几岁时候的事,但是清楚记得是上学之前。
那天我醒的比较早,天色还有些暗,我好像是被院子里软枣树(方言:君迁子树)上喳喳叫的灰喜鹊吵醒的。
我躺在床上,看着被烟熏黑的屋顶和墙,墙上脱落的斑驳墙皮,构成了各种图案,我想象着那里是一座山,那里是一张人的脸,那里是一只鹿,那里是一条狗……我正无限遐想的时候,我突然清楚地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从我家房梁上伸下来。
房梁下面放着一摞很高的煎饼,那个年代,我们那家家户户都有一摞煎饼,那摞煎饼是一家人小半年的口粮。
我看见那只毛茸茸的大手在煎饼上抓了一下,过了一会,那只手又从房梁上伸下来,又在那摞煎饼上抓了一下,但是房梁上我没看见其他任何东西,只看见那只毛茸茸的手从房梁上伸下来。
那只手有些像多年以后在动物园里才见过的大猩猩的手。
我指着房梁赶紧叫父亲:“大大(方言:父亲),他偷咱家nianing(方言:煎饼,这两个字实在不知如何写)。
”父亲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谁啊,哪里有啊,净胡说八道。
”还在被窝里踹了我一脚。
我又看见那只毛茸茸的手伸出来抓了一次,我再叫父亲,父亲没再理我。
我到现在都有那只手的印象。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怀疑是我看墙皮图案产生的幻觉。
4、黑橛子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还没上学,约四五岁。
记得那是秋冬交替之际,天气比较凉,农忙也已经过了,一个月亮非常明亮的晚上,我和父母在奶奶家玩的比较晚。
我家和奶奶家隔着一条大街,我家住在一个死胡同的最里边,回家要绕过我家屋子的后边。
我们从奶奶家出来,月亮已经超过树梢,高悬在天空中了,父亲背着我,母亲在后边跟着,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走到我家屋后的时候,我看见我家屋后那棵倾斜生长的大枣树下,路的正中间,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像是倒扣的一筐猪粪。
我指着那堆东西告诉父亲:“那里有一大堆猪粪。
”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是觉得有人在那里倒扣了一筐猪粪。
父亲看了一眼,他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父亲低声向母亲说了一句:“快走。
”我盯着那堆黑乎乎的东西,想趴在父亲背上,不知为什么,我却被母亲抱了过去,我们急匆匆的回到家里,一进大门,父亲立刻把大门锁上,赶紧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被洋匣子吵醒,父亲和母亲早就醒了,他们坐在床上聊天,我听见母亲问父亲:“昨天晚上在屋后头,你干嘛把孩子扭(方言:拧)哭?”父亲说:“我没扭他。
”母亲说:“你没扭他,那他怎么哭了?”父亲争辩说:“我真没扭他,正好好的我扭他干么?”可是我明明记得昨天晚上在屋后面父亲没扭过我,我也没哭过,他们为什么说我哭呢?后来和母亲偶然聊起这事,她还是说我莫名其妙的哭了,她就以为是父亲扭的,这时父亲都会极力争辩从来没扭过我。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没哭,父亲也没扭我。
过了几天,母亲听本家的一位二大娘说,和我家隔着一条小路的后邻居,那天晚上送邪神,也就刚办完送邪神仪式,我们就过来了。
左邻右舍都听见了我的哭声,都给我母亲说,不是父亲把我扭哭的,是被黑橛子吓着了。
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没扭我,我也没哭过。
至于那堆黑乎乎的东西,我还清楚地记得它模样,我一直觉得那就是一堆猪粪。
5、桃树上的人还是学前,五六岁时候的事。
东邻居的大门外,有一棵倾斜着长得很矮的桃树,树干有小腿粗细。
这棵桃树就是当地常见的小毛桃,结的桃子不能吃。
每逢春天,这棵桃树上就稀稀拉拉的开出几朵淡粉色的桃花。
初夏的傍晚,吃过了晚饭,父亲、母亲和东邻居家的大人们,在东邻居家大门口闲聊,我和东邻居家的孩子们追逐游戏。
正玩着,我看见倾斜的桃树杆上蹲着一个人,清晰的记得,那个人就是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看不清是男是女,就是一个黑乎乎的人形的黑影。
他不是趴在树上,也不是站在树上,而是蹲在树上。
我指着桃树告诉大人们:“你们看看,一个人在桃树上蹲着呢。
”一开始大人们没在意,我看那个人蹲在桃树上一动不动,我拉母亲说:“娘,你看看,一个人在桃树上蹲着。
”大人们停下聊天,母亲问我:“哪里?”我指着桃树上的人影说:“你看,那不是吗?他在桃树上蹲着呢。
”他们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看,立刻慌张的招呼孩子们回家,父亲和母亲拉着我赶紧回到家里,锁上大门。
很长一段时间,晚饭过后,都没有人敢在东邻居的大门口玩。
后来,我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什么也没看见,我不信,再追问,母亲就骂我:小赊孩子,别胡说八道。
问父亲,父亲也说没看见什么,我不满的说:那你们干嘛都跑回家?现在我突然明白过来,人们最恐惧的就是不可知的东西,就因为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才吓得跑回家的。
即便是我当时随便说的瞎话,他们也会害怕。
6、墙根的妇女 应该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麦收刚过,晚上村里有电影,那时候的电影不是《地雷战》、《地道战》就是《南征北战》。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吵了几句嘴。
他们吵架简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小时候我经常被他们吵架聒醒。
父亲和母亲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左邻右舍到我家劝架也是很经常的事。
他们这个习惯到我成年结婚后也没改,一直吵到父亲去世,真正是吵了一辈子。
印象里那天放的《南征北战》。
电影散场后,父亲背着我回家。
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月色朦胧,月亮有一个很大的晕。
到了家门口,父亲一摸大门是锁着的,母亲还没回来,一直都是母亲带着唯一的一把钥匙。
父亲背着我到母亲经常串门的几户人家找,没找到母亲,又背着我回到大门口,一摸门锁,还是锁着的。
父亲嘴里开始不干净了,骂骂咧咧,焦急地说:“你说你娘去哪里了,还不回家?”这时,我看见西墙根有一个妇女,高矮跟母亲差不多,好像在哭,拿着一只白色的手帕在擦眼泪,我指着那个妇女说:“俺娘不是在那里吗?”父亲说:“在哪里?”我指着说:“在那里,还光擦眼泪呢。
”父亲看了一眼,也不说话,背着我转身赶紧走出胡同。
父亲找了好几家,终于在一个母亲平时很少去的刘姓电工家找到母亲,找到母亲的时候,母亲正和人家聊的起劲。
父亲说了母亲几句,母亲反驳了几句,一起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的紧张,父亲左顾右盼,轻手轻脚,但是我没再看见西墙根的那个人影。
现在想起那个人影,感觉就像现在的投影仪投射到石头墙面上一样,不是很清楚,也看不清面部,但是手里擦眼泪的白色手帕,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7、车祸紧挨着村庄的这条公路,是国道,不管白天黑夜车辆都很多。
在十多年前,从我们村西边上山的那条路口起,一直到老苹果园东边的那个路口,不到一公里的这段路,是车祸不断。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车祸,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西边某村的一个牛贩子,在村口出的车祸,当场死亡。
当时我也跟着凑热闹,去看事故现场,看见了一大滩鲜红的血,恶心的我反胃至少一个月吃不下饭,到现在我还能想起那场景,从此,我再也不围观任何事故现场。
从这起事故开始,开启了这段路的噩梦模式。
其后,本家的一位哥哥,也发生了非常惨烈的车祸,我清楚记得,他死在一辆车门上印着“**十一局”的渣土车轮下,他当时骑的自行车都被撞的扭曲成一团。
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特别是下点小雨的夜里更是恐怖,经常在睡梦中被公路上剧烈的撞击声响惊醒,惊魂未定的时候,还会接着传来接二连三的撞击声,每一起猛烈撞击的声音,都是一起惨烈的事故。
这时,父亲和母亲都会赶紧起来,母亲惊魂未定的看着惊慌的我,父亲赶紧穿衣出去,村里的很多大人都会赶紧向事故地点汇集,帮忙救人,当然也有个别人想趁机发点横财。
几乎每次事故都会有人死亡。
最惨的一次,是一辆运输大豆的货车,好像是江苏的,车上三人,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夫,全部当场死亡。
当时一对老父妻来到现场,老父已经欲哭无泪,老母亲哭的数次昏死过去。
老父亲抱着老母亲说:“别哭了,这就是命啊。
”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写到这里,我还是难受的几乎写不下去了。
更可气的是靠近事故现场的几户人家,偷了不少大豆,说是偷,其实就是当着事主的面明抢。
当时,老夫妻哀求偷大豆的那几户,不要再偷了,人都没了,货物再保不住,赔不起啊。
当年偷大豆的那几户人家,现在过得并不好,有三两家已经家破人亡,从村庄里消失了。
一个按辈分应该叫婶子的妇女,前年十月八号傍晚,下了点小雨,在牛贩子出车祸的地方,被一辆越野车撞了,当时这位婶子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婶子的两个儿子都过去看,愣是没认出来是谁。
丈夫去村里给别人家帮忙,还说南边公路上有一个疯子被车撞死了。
第二天,婶子的二儿子等婶子送大孙子上幼儿园,顺便照看小孙子,等到十点多也不见婶子,兄弟二人到处找也没找到。
村里有人已经认出来是谁了,丈夫再去车祸的地方看热闹,有人告诉丈夫,你在仔细看看,到底是谁?丈夫靠近仔细一看,才认出来是到处找不到的婶子。
因为昨天傍晚下了点小雨,她披了一块床单,又穿了丈夫的一双拖鞋。
都以为是个男性精神有问题的人,没想到是婶子。
后来,村里有人出面,组织全村捐钱,举行了一次比较大型的祭奠仪式之后,又赶上公路翻修,路况远比以前好得多,这段公路出的事故渐渐的明显变少了,一年也见不了几次。
但是,事故多发地明显东移了,移到了东边的那个村庄,那里开始三天两头出事。
印象比较深的一起事故,是东边那个村的亲姐妹俩,穿着新买的高跟鞋,姐姐用自行车驮着妹妹,被一辆货车碾压,姐妹二人当场就没了。
后来又过了两三年,那个村庄也举行了一次比较大型的祭奠仪式,事故多发地又东移了,移到又下一个东边的村庄。
在那里出现过一次更为严重的事故,某市的一个考察团,据传职务还不低,所乘商务车出现事故,一车六、七人,无一生还。
后来听说他们村也进行了祭奠仪式。
不知道现在是否东移又东移,是否都已平安无事。
有村民说,是先死的冤魂在作怪。
如果真的有妖魔鬼怪作乱,导致车祸不断,那些因之而死的人,为什么成“鬼”之后,对那些妖魔鬼怪不加报复,还放任它们继续为祸世人?我不能理解。
也有村民说,可能是地下河导致的磁场紊乱,造成的事故多发。
现在那里事故明显的少了很多,当年出现那么多事故,也可能和当时的路面、车况有关。
现在路修的好了,制造车辆的技术也比以前有进步,这都是事故变得越来越少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