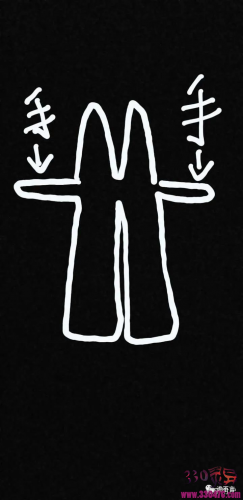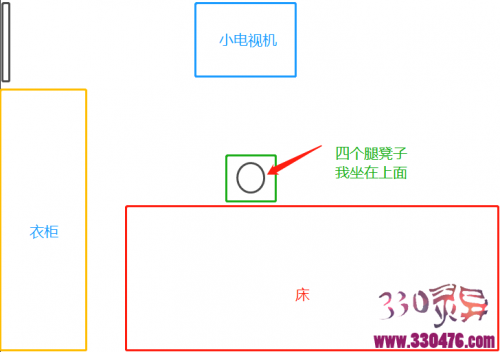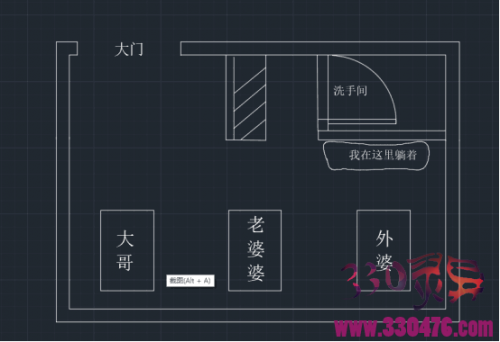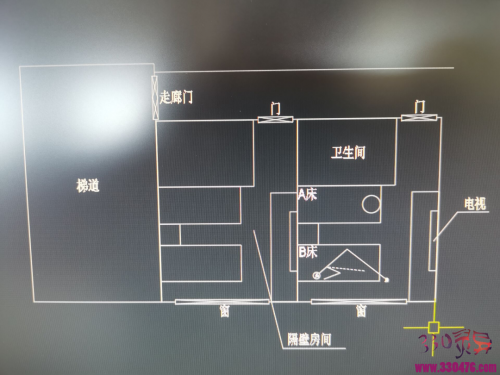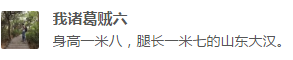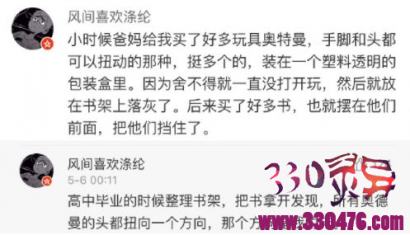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太湖流传着一个关于“太湖怪声”的传说。
传说在太湖某片水域,每到半夜,水下会突然传来各种怪声。
后来有人半夜划船过去,偷偷用录音机去录了音,回来整理了一下,发现那些声音很古怪,像一群人在窃窃私语,还夹杂着一些古怪的歌声,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事情在当年影响很大,现在你去苏州平龙山一带,有些当地的老人还记得这个事情。
不过,七八十年代气功热,什么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外星人、水怪、毛孩之类的,到处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当不得真了。
我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因为有个亲历过这件事的老渔民,亲口给我讲过这件事情。
这个渔民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是当年怪声事件的亲历者,还是当年用录音机录下来怪声的那个人。
这个渔民姓吴,叫吴德叔,他当年在太湖录下怪声时,还是四十多年前,还是个棒小伙。
他是传统的渔民出身,以船为家,吃住都在船屋。
渔民也像一个小江湖,有渔帮,渔会,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和禁忌,很神秘。
58年成立人民公社,渔民也改编进了渔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改名叫“渔业大队”,设了四个渔业生产作业组,他当时分在吴县(现在的苏州吴中区、相城区,以及虎丘区部分)管辖的西南太湖。
当时西南太湖有几个小岛,包括现在很火的“东山岛”、“西山岛”,岛屿西边有座小山,叫做“平龙山”。
平龙山下的一片水域,就是当年发生怪声的地方。
吴德叔当年就是在这里,录到了怪声。
他说,自己当年也是被骗的。
当时他们生产队一个小领导找到他,说组织上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深夜划着小船,去平龙山下的水域录一些东西。
平龙山下的水域晚上有一些怪声,他也听说过,不过他并没有太在意。
做渔民久了,他知道,最古怪神秘的其实是风声。
风穿过石洞,穿过芦苇,穿过水浪,声音都是千奇百怪的,什么声音都有可能发出来,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并不稀奇。
小队长交给他一个很高级的国外录音机,还是防水的,让他把录音机固定在船头,并且嘱咐他,从他下水那一刻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录音机都不能停。
还让他不要告诉别人。
他晚上去了几次,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后来到了第四次还是第五次,那声音才出现。
他记得那天月亮很圆,他把小船划到水里,没过多久,就听到了那个声音。
他说,那个声音刚开始,还真是有些可怕。
他问,你有没有听过猫叫春,还是几百只流浪猫一起叫那种?那种声嘶力竭的惨叫声,夹杂着几声特别尖锐的叫声,真像冤鬼索命一样恐怖。
他当时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
他吓了一跳,差点儿把船桨掉到水里,后来听了一会儿,那声音就渐渐变了。
后面的声音很奇怪,它不光是哭声,更像好多人在水下窃窃私语,在密谋着什么,声音很杂乱,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像底下有个集市,好多人在那吵闹着,呼喊着,大笑着,吵吵嚷嚷的,但是他眼前是一片黑黢黢的水域,没有任何人,所以感觉特别怪异。
后来底下就开始传来机器声,嘟、嘟、嘟、嘟、嘟那种声音,声音急促且刺耳,有点儿像连续的汽车喇叭声,不过也不太像,要比喇叭声更加尖锐,而且声音越来越响,堵住耳朵也能听见,像是顺着骨头缝往他脑子里钻,像打桩机在他脑袋里哐哐哐打夯,把他震得差点儿吐出来。
他好多次想走,但是想到小队长说务必要录满三个小时,又想到小队长承诺给他的工分,他忍了又忍,硬是坚持下来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湖上突然起浪了。
太湖的平均深度其实很浅,还不到二米,但是有些水域又极深,甚至深达五、六十米深,像底下出现了一个个深井。
而且它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现象,比如无风起浪。
无风起浪,指的是太湖上明明一丝风也没有,突然就涌起了大浪,而且是滔天巨浪,能瞬间把小船打进水里。
有时候又会突然涌起浓雾,刚才还清清爽爽的湖面,突然就被浓雾笼罩了,打着灯笼都看不到前方。
然后过段时间,突然呼啦一下,像有人拉开了窗帘,浓雾瞬间就散开了,月光洒下来了。
有老渔民就说,太湖底下有巨怪,这些浪花都是它在水底下折腾,那雾气就是它鼻子里喷出的白气。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
总之在太湖上讨生活的渔民,最怕的就是无风起浪,以及突然出现的浓雾。
结果这两起,吴德叔全部遇上了。
几乎是一瞬间,湖面上就笼罩上一层浓厚的雾气,他船上那盏煤油灯,完全不起作用。
而且湖面上波浪滔天,一个浪花接着一个,几乎要把小船给抛起来。
他第一时间用雨布将录音机包裹好,塞进船舱暗门里,接着用缆绳把自己牢牢绑在了船上。
他知道,遇到这种天气,人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只能把自己绑在船上随波逐流,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就看龙王爷要不要收人了。
小船仿佛无根的浮萍,在太湖上颠簸着,跳跃着,不时被浪头抛起,越走越远,也不知道漂到了哪里,他吐了好几次,最后在颠簸中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发现浓雾早散去了,而且天边已经发白,天都要亮了。
在他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小岛,小岛上挂着几盏灯笼。
有灯笼就有人!他兴奋了,船桨早丢了,他就用手划着水,拼命朝着小岛划过去。
他划着划着,终于要划到村子了,就在他看清楚小岛的瞬间,猛然停了下来。
因为在那个小岛外,密密麻麻站着好多人,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不,确切地说,这些村民眼睛里根本没有他,他们的眼神穿过了他,看着他身后。
他身后有什么?他想回头,又不敢回头,同时心里也暗暗嘀咕,没听说太湖岛上有什么住人的村子,而且这些人的穿戴也不对啊,这他娘的该不会是个鬼村子吧?太阳渐渐升起来了,船舷上漫上了一层淡淡的霞光。
他终于放心了,鬼怕日光,现在日头都出来了,他还怕个球?扭过头,就看见太湖上冉冉升起了一个红煤球大小的圆球,这就是太阳了。
他一阵欢欣鼓舞,想着太阳终于出来,他终于得救了!他想高声呼唤几声,但是张开嘴,嗓子眼里干干的,没喊出声音。
他觉得有些不对,又想不到到底是哪里不对。
他想了又想,终于明白了:是岛外的人。
那些人惊恐地看着太阳,或者说看着他身后,不断往后退。
他忍不住又一次转过头,终于发现了问题。
原来,有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了,可是水里还有一个太阳!这世上怎么会出现两个太阳?!但是千真万确,水下的确还有一个太阳!伴随着第二个太阳出现,他发现,太湖像沸腾了,往外冒着咕嘟咕嘟,冒着大水泡,各种鱼儿疯狂从水下蹿出来,甚至朝船上、人身上撞去,撞得整条船砰砰作响。
他吓得赶紧要撑船靠岸,却发现岛上的村民突然间消失了,面前只有黑黢黢的礁石。
他犹豫再三,要不要上岸,这时身后有什么东西碰了碰他,他回过头,发现身后是一个人,又像一个怪物,冷冷地看着他。
然后那个似人似怪的家伙,朝他说了一句话。
他的声音非常急促,像是催他快走,又像在追问他什么,不过他没有听清楚,因为当时一个大浪打来,把他连人带船打到了水下。
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是太湖下一片璀璨,一轮太阳从水下冉冉升起。
……关于吴德叔当年到底在太湖里听到了什么,那个似人似怪的东西又是什么,太湖底下出现的第二个太阳又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因为经历了这件事后,吴德叔人已经疯了。
当大家看到他时,就发现他赤裸着身子,在太湖边上拼命嚎叫着,奔跑着,嘴里喊着大家都听不懂的什么话。
据说,他身上像被电烙铁烙过,留下了许多形状怪异的伤痕,这些伤痕有棱有角的,像被什么精密的机械零件烧红烫伤了一样。
他是孤儿,也没有家人,政府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在里面呆了很多很多年,后来终于好了,不过却开始怕水,尤其是太湖,所以政府就安排他去了建筑工地看门,偶尔也帮着干点儿活。
他从此成为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每天看门、拉车、搬砖、喝酒,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不管天多热,他始终穿着长袖衣服。
只是在偶尔冲凉时,他身上丑陋而怪异的伤痕会把别人吓一跳。
再后来,改革开放,原来的国营建筑公司被一家民营公司收购了。
那家民营公司老板和他聊了聊,觉得他是个老实人,就让他去了自己家,帮着做做饭,主要是带孩子。
这个收购国营建筑公司的民营老板,就是我父亲。
吴德叔带的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他靠做建筑起家,开始做旧城改造,后来做古建筑修复,算是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商。
当年我父亲见吴德叔老实诚恳,就让他去了我们家,偶尔帮着做做饭,主要还是带带我。
我当时还小,也就六七岁,精力旺盛得像只野猴子,每天在外面疯跑,直到筋疲力尽了,才让吴爷爷背着我回来。
我至今还记得,在无数个黄昏,太阳温暖地照在我身上,周围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以及远处太湖的潮湿的腥咸的气味,吴爷爷背着我,顺着长满了野花和小草的小路,慢慢走回去。
我又累又困,却坚持着不睡,就懒洋洋地枕在他肩膀上,看他肩膀上的伤痕。
他的伤痕密密麻麻地环绕在身上,形状很规则,还泛着蓝黑色的金属光泽,看着非常怪异。
我当时很好奇,他就说了太湖怪声的事情,还让我帮他保密。
吴爷爷很怕打雷,每次要打雷,他都要关紧门窗,甚至连门下的缝隙都要堵得严严实实的,整个人都蜷缩在被窝里,仿佛生怕雷电会顺着床底下蔓延过来,把他抓走。
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开始的时候,吴爷爷还经常被各种研究机构叫走,做一些实验之类的,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摧毁了一切思潮,各种商业蓬勃发展起来,全国人民一致向“钱”看,再没人关注这种事情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见风似长,很快长大了,吴德叔也老了,而关于太湖的神秘故事,并没有结束。
再后来,我个人也经历了大学退学,北京流浪,后来机缘巧合去了深圳,在腾讯做了五年网游后,又去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做了高管。
当时我还很年轻,也是公司最年轻的高管,还写过几本破书,香车美女,快意恩仇,谁还耐烦记得当年那些小事,关于太湖的种种神秘故事,早就被我抛到了脑海里。
只是偶尔喝多了,午夜梦回时,我才会模糊地想起,在好多个夏夜,我们在老树下点起篝火,篝火噼里啪啦响着,草虫和青蛙率性地叫,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的味道,泥土和青草的香气,吴爷爷摇着蒲扇,慢悠悠给我讲着太湖里的故事,太湖怪物,太湖毛人,太湖里升起的神秘太阳。
我还记得他每次都会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尾:太湖底下的东西,要压不住了!而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二十多年后,我会用那样怪异的方式重返苏州,而关于太湖,或者说关于苏州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