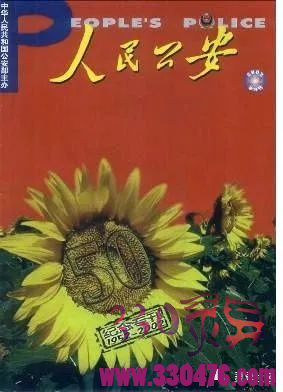村头张奎生就从小喜爱玩乐器,二胡、笛子、萧都会,以前村里啥都缺,就是不缺桐木、芦膜、蛇皮、马尾巴,奎生买不起就自己手工制作。
只要闲下来,不论是阴天或晚上,张奎生就用他自制的乐器,吹弹拉打,轮流一遍,夜深了就不停地吹箫,那萧声幽怨而悠扬。
尤其在月色灰暗的夏夜,那股悲戚与苍凉,直逼得人愁肠欲断。
那低沉似吹埙的啸声,被风牵着,挤进东邻西舍窗户,弄的满庄上人都不安宁,张奎生那几年婚姻高考都不如意,现在想来也许是借吹箫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吧。
但农村人忙活一天,早就疲惫不堪,可没几个能去欣赏大哥那愁肠满节的心曲,大多把它当做催眠的夜曲。
张大伯心疼张奎生,又担心他扰人,看到我们小弟几个都喜欢跟张奎生玩,就给我们有声有色地讲了个夏夜在野外吹箫会招鬼的故事,说来给大家听听。
说以前在老家,看瓜的棚子一般盖在地中间,土墙垒起,四面留窗口,上面苫上茅草,遮雨不挡风,便于看守。当然,现在也没有几个混小子再去偷瓜桃梨枣的了。
你们知道庄东头憨老张为什么是个光棍汉吗?老张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说媳妇挑东家拣西家,横竖不合他适,整日沉迷于乐器,看了大半辈子庄稼,就是在一个夏夜里在漫野湖瓜棚里吹萧,招到鬼了,被吓憨的,打了一辈子光棍,老来成了五保户。
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了,总之是在一个夏夜,老张独自坐在野外瓜棚里网床上,床头放杆鸟铳,瓜吃多了睡不着,于是拿出长萧,双手捏着,放在唇边,闭上眸子,不久那空妙绝境、若即若离的的萧声,就在野外远远近近飘扬起来。
俗话说,箫声咽,笛音远。在静谧的夏夜,又是野外,那萧声穿透薄雾在野外丝丝缕缕地飘荡,如泣如诉,不招来孤魂野鬼才怪,平时晚上在家,老张只要演奏乐器,蚯蚓蛐蛐都会跟着应和,但那晚老张啸声刚起,周围的虫鸣声就都停下来了。老张一曲连着一曲吹,吹累了,就抽出烟袋来,慢条斯理地吞着云吐着雾,那缕缕烟香随着缥缈的雾气在空气中荡了很远,抽着抽着就打盹了。
就在老张迷迷糊糊之间,从瓜棚西面窗户撒进一把补土了,老张以为有人偷瓜,忙起身走出棚子,围着瓜棚转了一圈,除了明亮的月光和静谧的夜空,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老张傻眼了,说是做梦吧,感觉自己并没睡着,说是打臆子吧,脸上脖颈还有土粒子。
老张回到棚内网床上,眼瞪着西窗口,静静地按烟抽,不敢睡。
就在老张惬意在浓浓的烟香味四处飘的境界里时,从东窗口又撒进一把灰土,老张放下烟袋,提着鸟铳走出棚子,像刚才一样,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老张纳闷地回到棚内,发现烟袋挪了地方,烟袋锅里的半袋烟好像被抽完了。
老张浑身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会是谁呢?和自己开这样瘆人的玩笑。毕竟再好的月亮地也赶不上雾阴天,有明亮的月亮照着总不一样,但那夜偏偏是天上月朗星稀,地上雾气连连。
那时老张年轻,玩心重,紧张但不害怕,于是老张重新装上一袋烟,静坐在网床上,眼也不眨地盯着窗外,老张屏住呼吸,等了半天,外面了无动静。
不久,起了微风,一团乌云飘过,遮住了月亮,薄雾散了点,月光也暗淡不少,老张有点乏困,正感觉要迷惑打盹间,就觉瓜棚门前不知何时悄无声息的站着一个黑大汉子。
老张毕竟不是小孩子,知道遇见了怪物,边思谋怎么脱身边说:“好汉,想吃瓜就去摘,想抽烟就坐下”。
那大黑汉子于是盘腿坐在老张门前,手指着老张挂在床头的烟袋,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想抽烟。
恐惧过度会产生保护自己的本能,老张对坐在面前面目不清的黑大个子说:“不好意思,这个烟袋窝有点小了,我给你换个大的吧。”
黑大个子没有吱声算是默许。老张举起怀中鸟铳,对着怪物说:“你含着,我来给你点火。”
待老张把火药捻子点着以后,老张双手举着枪把,对怪物说:“赶快吸吧!”
那怪物吸了半天,没有烟味,正待发作,那鸟铳“嘭”地响了,那黑汉子倒地后,化作一地大大小小的火团子,在半人高的空中,围着瓜棚,蹦来蹦去,飘来荡去,很是诡异。
老张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闭眼,连滚带爬跑回家里,栓紧大门,顶上杠子,蒙在被里,牙齿打颤,浑身发抖。
第二天,庄上人带上招钩粪耙子一起来到瓜地,围住瓜棚,只发现瓜棚上苫的草被拽的乱七八糟,扳的满地都是,瓜棚内老张的衣物床铺,也被抓撕的凌乱不堪,老张说的那怪物谁也没看见。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自从大伯讲了这个故事后,我发觉张奎生吹箫少了,有时间就看看书,看累了就拉拉二胡。大哥后来考上了师范,现在还在一所中学教音乐和体育,估计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