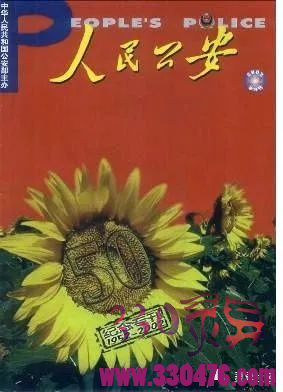荒郊白骨卧枯莎,有鬼衔冤苦奈何。
半夜数声凄枕席,十年几度惨干戈。
年,我和朋友在新疆租了两千亩地种棉花,招了二十几个工人做长工。这些工人都是少数民族,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民族的名字,也有汉人的名字。由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名字长而且难以理解,喊起来我也喊得不准,所以我从来都是叫他们的汉人名字。其中一个叫阿九的,印象让我特别深刻。
我们播完种后,晚上就开始放水。由于用的是滴管带,请的临时工有的不负责,常有接头脱落的现象,所以我就带了几个男工打着手电四处检查。阿九只有一只手,他干不了这样的活,所以我叫他回去休息。
那天晚上很冷,我们检查完一遍后,每个人基本上都被喷出来的水淋湿了,就在地边生了一堆火。那时候已经凌晨一点过了,水情也基本稳定了,我只留了两个手脚麻利的小家伙陪着我守地,我们一边烘衣服一边聊天。一个叫阿力的脱下上衣来烤时,我注意到他胳膊上系了一根红绳子。
“你系这个红绳子是辟邪的吧?”我问他。
“是的,阿妈说晚上有鬼,系根红绳子就没事了。”阿力回答我说。
“你们相信有鬼么?”我笑着问他们,说实话,虽然我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并不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有时候我相信有,有时候我觉得没有。

“老板,那是什么?”我们的话题还没聊完,阿力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我顺着阿力手指的地方,一个黑影左躲右闪、轻飘飘地朝我们走过来。不会吧?说鬼就真有鬼来了。
“谁?”我用手电晃了一下,壮起胆子大声问道。
对方没有回答,两个小家伙也吓得站起身来,紧张地看着前面。因为我们的地不远处就有好多坟,新疆那边有的地方本就特别荒凉,我又是头一年来这,所以我也格外紧张。
“鬼!”另一个小家伙阿杨声音都发抖了。
“是谁?!”我又大喊了一声,对方还是不发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
那个黑影还是左躲右闪慢慢地朝我们的方向飘过来。“拿镰刀!”我吩咐两个小家伙说道。两个小家伙动作倒是挺麻利,一人迅速找了一把镰刀攥在手里。我想,要真是鬼的话,镰刀恐怕一点威力也没有。不过有个武器拿在手里总有点安全感。
那个黑影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到手电筒能照清了,我去!原来是阿九!我真想踹他两脚。不过见阿九拎了几个饭盒过来,我的愤怒一下没有了,转而心头一阵感动。他们这些人真好,这么晚了还没睡,还惦记着我们,给我们做了些宵夜送来。我还是忍不住用平和的语气说了阿九两句:“阿九,刚才你把我们吓得半死。下次不要这样了!”阿九只是傻呵呵地笑,用极其生硬的普通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就没说。”好吧,这个解释我勉强接受。阿九说的倒是实情,他们说起普通话来的确很费劲,很难说一句完整的话,他们说话我基本靠猜。哪知,我只对了一半。阿九不会说普通话不假,但这家伙就是爱装鬼吓人。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也慢慢了解到阿九是个乐观、爱开玩笑的人,其他工人也常和我讲阿九晚上爱扮鬼吓他们。不过他们也不是告状诉苦的那种,而是当成开玩笑,大家都挺开心的。我也没在意,反正他不会来吓我,哈哈!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为我的大意付出了代价。
一天早上还没上班,工头就来告诉我,说阿九出事了,他们要结工资回老家。阿九虽然只有一只胳膊,但是他和他老婆干活是最卖力而且效率最高的,每个阶段评奖我一般都是发给他们两口子。现在棉花还没有长成,人力都是刚刚好的,这一走就是两个好手,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我见到阿九时,又好笑又心疼,这家伙的嘴全歪到左边去了,左边的脸还在不断的抽搐,就跟电视上那个赵四一样。
“阿九,咋搞成这样了?”我忍住没笑出声来。
“老板,昨晚夜里起来上了个厕所,老是觉得有个影子在跟着我,但是又看不见。今天一早起来就这样了。”阿九可怜兮兮地对我说。
“他是闯到鬼了!”一个年纪大的老工人说道,“他这个要回老家去杀大公鸡请人跳大神才行的。”
我估计是这家伙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中风了,如果继续留他,耽误治疗了会多些控制不了的麻烦,所以只好把他的工资结了,让他回家。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新疆,也失去了阿九的联系方式。我一直希望他真是闯鬼了,请个跳大神的就能治好。不然的话,他们两口子挣的那点钱恐怕只能治病了。他们,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