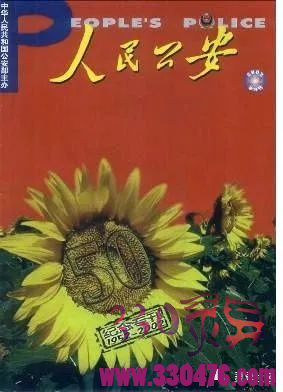我妈的老家有个老人,一辈子没有结婚,独居在远离村庄的山脚下。
身体很好,六十多岁还能上山砍竹子编竹椅之类的东西拿去圩上卖,偶尔给人选日子写请帖之类的。
相传曾经是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常有外地的豪车停靠在村里,西装革履的老板走烂泥路亲自上门请他,但没听说有人成功过。
我小学时有一次在舅舅家做客。那天一直下大雨,他却突然上门讨水喝。
我本来正闹着要回家,我舅舅已经去拿了车钥匙准备送我了。无奈只能又返回去给他倒水。
那天我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了山体滑坡,我隐约还听到了山体垮塌的巨响。算算时间,如果不是他耽误的那一下,大约我就在里面。
后来大概我初中,21世纪初。听说他死了,死在自己常去砍竹子的山上。
死法非常传奇——他在自己家后山滑倒了,削尖的竹桩刺入了他的咽喉,把他钉在了地上。
再后来听别人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接了一个老板的钱,90年代末,说是拿了五位数。不记得钱拿去干了什么了。反正就是给人出了主意,别人事前事后送了他两次钱。
家里的老人都说他这辈子泄露天机太多,原本缄默寡言,过了几年安生日子。到最后还是没忍住拿了不该拿的钱说了不该说的话,被老天彻底封了口。
他可能并不是有什么奇术,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只是多种巧合的叠加。但他的经历确实很是传奇。
还有另外一个老人,是我老家的。但并不是什么算命先生之类的。只是个普通的老人。
不过他生于1896年左右,于2004年才过世。经历了三个世纪,完整见证了历史动荡的那些年。这就已然是一种传奇了。

他和每个老年人一样喜欢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他90岁高龄还可以自己提个水桶去打水,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据我所知他也是无儿无女,没有自己的家,住在我老家祠堂的偏方,靠同宗族的其他人接济为生。
他心情好的时候会唱戏,就算没有人看,也乐在其中。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分饰数角,声音可男可女可沧桑可稚嫩,兴致上来了谁也不能叫他从戏里出来。
他五行周易之类的张口就来,我们老家的人基本听不懂,但是本能的觉得他很厉害所以很尊敬他,很多人家里有小孩出生都找他取名。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给抓去当脚夫,给当时某个大地主运贵重中药材,遇到打劫的,他带着自己那批药材跑了。
后来饿了吃药材,吃了难受就大量喝水。艰难逃生,在外避了多年才回家。
他认为就是那批药材那段生活带给了他长寿和健康。我们那有人生病了喝中药,他闻个味就嫌弃现在的药太假,和他们那时代不能比。
我们那很多人是信的。后来我觉得这不科学,但不敢在他面前说。不过他确实长寿而且健康。

父亲是个工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他们那个年代,能吃饱喝足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有一年,家里经济很拮据,又要供我们几个读书,父亲就随老乡到天津打工,因为没多少文化,就给一家化肥加工厂当工人。
这个化肥加工厂建在荒郊野外,老旧的厂房后面,是一片芦苇塘。
一天,因为加工厂要赶一批货,父亲和几个工友当晚没有回去,连夜装卸化肥。
深夜大概十一点多,正在装卸化肥的父亲突然听到芦苇塘后有婴儿的哭声,开始以为是野猫叫春,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大半夜野猫叫春的声音很像孩子的叫声,也比较恐怖。
但仔细一听,不是野猫叫春,确实是婴儿的啼哭声,声音时大时小,不时还拉长着哭声,在寂静的荒郊野外格外响亮。
我父亲看了看几个工友,几个工友也一头雾水。那个年代,农村人都很老实巴交,很淳朴,心想有孩子当然要救啦!
于是放下手中的活儿,商量着去看看究竟。几个人找来一把手电筒,循着声音去芦苇塘后找啼哭的婴儿,奇怪的是,每次就要接近时,声音就停止了。
几个人一离开,啼哭声就又开始了,找着找着,突然听到货车司机从远处喊道:你们几个快回来!快点!
几个工友正想往芦苇深处走去,听到司机的喊声,就退了回来。
后来听那司机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天津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日军细菌战部队还在此建立了研究所。
这里曾死过好多无辜的贫民,当年那些被日军凌辱过的老百姓,被绑在木桩上,顶着白天的烈日晒一天,不给食物和水,晚上喂蚊子!
听当地老人讲,那些喝饱血的蚊子都能撑的从身上滚下来,可怜的老百姓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这个荒郊野外的老厂房,除了存储货物,平时根本没有人影。

我姥姥家在金乡县,也就是大蒜之乡,那是在70年还是80年初,我记不太清了,那会儿村子里都是有生产队的,我二姨就在生产队干活。
当时村里组织人打井,因为这样浇地方便不用再挑水,但是打井的位置在一户人家的坟地,当时那户人家是坚决反对,各种找大队负责人找村长。
那个时候就是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就说你这种观念不行,村里压根不理他该怎么打井怎么加井!
打井开始挺顺利的,但是过了几天有人晚上去地里干活,就听到那个坟地有人说话:别打了别打井了!隐隐约约就能听到这句话。
其实当时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事不该继续做,但是当时提倡科学,传那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厉害了会被人打的。
后来井打好了,我二姨与一个跟我辈分一样的姐姐跟着生产队晚上浇地,当时我二姨走在路上,跟在我那个姐后面走,但就是看不见那个姐的头。
当时二姨也不敢声张,觉着是不是累了看花眼了,但是别人的脑袋都可以看到,就她的看不到,我二姨安慰自己,觉着是天黑了看不清。
后来浇地中间坐下来歇一会,当时从井里抽水的水泵也关了,我那个姐坐在水泵旁边,可是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水泵自己打开了,然后抽水管子没有固定就乱摆动,一下把那个与我辈分相同的姐头给打掉了。真的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