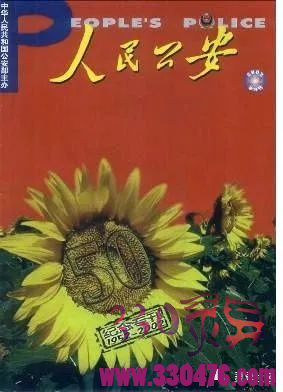夜深了。
高生睁大眼睛,望着朦胧胧的帐顶,一缕幽香,仿佛冬日肃杀时节窗外的寒梅,给百无聊赖的生活带来了色彩和希望。他摸索着,从枕边抽出那方巾帕,香气骤然浓郁了些,他无意识地把巾帕贴在胸口,拥入怀里。
“唉,江城,江城……”
江城是个小姑娘的名字,他上一次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还是两条扎着红绳,蹦跳跳的丫角小辫。
十年前,东村一个姓樊的教书先生到这里开蒙馆,租了高家的空房安置家口。乔迁那天,高生跑出去看,正见到一个小女孩,鼻头翘翘的,扎着两根小辫,倚在樊先生腿边,好奇地向他望来。
“江城,”樊先生唤着女孩小名,摸摸她的头发问道:“要去玩耍么。”
小女孩点点头,蹦蹦跳跳奔向高生,于是高生得到了一个年纪相仿的玩伴。
高生的玩耍生涯实在没有维持太久,年华像一只一只土囊,不仅堆在了高生身上,也在青梅竹马的玩伴间越堆越高,高生的功课越来越繁重,江城受到的教育,也渐渐不许她抛头露面了。

几年后,樊先生举家搬走,高生始终未曾见到江城最后一面。不过多年的隔膜,高生对此亦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况且他的精力,需全副用到应付窗课上。
十四岁那年,高生考中秀才,进入临江府泮宫读书。虽说进学,其实是不必去上学的。秀才们大抵都待在家里,要么出门交游,有境况不好的,便需靠着这一点功名的资本筹谋生路,为人西席,教授子弟,或者依人作幕,充当方面长官的文案客卿。
高家家境殷实,衣食无忧,毋庸高生出外谋生。老父的心思,是打算趁早替他结下亲事,从此好心无旁骛,潜心用功。
高生一表人才,加上未及弱冠就已经是秀才了,前程当真不可限量,当地富室有女待嫁的,无不以为佳婿,纷纷委托冰人说媒。但高生眼界颇高,寻常姿色根本不能入目,高家又只此一根独苗,倍加疼爱,因此婚姻虽是「父母之命」,高生既不肯,父母亦不忍拂逆,几年之间,却媒无数,南邻北里都在猜测,究竟要是个怎样的姑娘,才能中这位小少爷的意?
一天,高生出门访友,辞归之时,已是黄昏。他踽踽走进条窄窄的小巷,斜阳映照下,抬头看见巷陌彼端,迎面走来一个修长婀娜的影子,远远望去,如同身披一层金辉,风华绝俗,不可方物。高生心旌摇荡:“世上竟有这般颜色!”但到底年轻脸嫩,不由自主地踧踖起来,忙低下头去,不敢正视。行到近处,余光所见,那女郎蓦地立住了脚,偷眼望去,只见女郎美目中射出错愕之色,怔怔盯着自己,似乎欲语还休。高生大奇,忘记了害羞,抬起脸仔细一瞧,那女郎的眉目霎时同久远记忆中的丫角小辫合而为一,全身剧震,脱口问道:“你是江城?”
女郎眸子里荡漾开无边喜悦,低眉浅浅一笑,却不答话,手牵着一个只有垂髫年纪的小丫鬟,慢慢径向前走。
高生知道,以当时的礼教之防,在路上同女孩子搭话是件极不得体的事情,倘若女孩子随便回话,更是会被指为不够「端淑」,于名誉大有妨害。江城的父亲是个老儒生,家教必定严格,是以江城不开口,并非不肯,而是不能。
然则难道就此错过?他突然灵机触发,一声咳嗽,故意将自己的巾帕遗落在地上,假装不知而去。只听那小丫鬟在身后轻轻说道:“小姐小姐,那个人的帕子掉了。”跟着便听江城道:“这位相公的东西我们不能要,快还给他。”高生一喜,放慢了脚步,小丫鬟果然追了上来,举起一方巾帕,拦在路上道:“相公,你的帕子掉了,我家小姐叫还给你。”高生道谢接过一看,巾帕的样式,却不是自己那方,而清馨幽幽,沁人心脾,尚带着美人香泽,不禁大喜——这无异于佳人回应了心迹!
高生飘飘然似欲飞起,一路足不点地奔回家,这天夜里魂牵梦萦,眼前全是江城看向自己那款款情深、亮如星辰的眼眸。
翌日,高生找个由头,同母亲谈起自己童年的往事,话题渐渐扯到江城,于是没口子的夸赞江城当年如何乖巧可人,最后表示,希望娶得江城为妻。
母亲笑道:“这么多年,真难为你竟没忘旧情。樊家小姑娘确然是个美人坯子,不过门户却不大当对,那位樊先生一辈子南北漂泊,连处自己的房产都没有,他的女儿怎能是你的良配?”
高生焦急道:“门户不当对又有何妨?樊先生处世端谨,士林楷模,江城幼承庭训,家教必然是极好的,嫁进来便是贤妻。我……我总之非她不娶,绝不后悔!”
母亲很诧异地瞧着儿子,半晌才道:“好罢,不过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要跟你爹商量。”
父亲的态度比母亲更坚决,执意不允,高生大失所望,从此食不下咽,夜不能寝,悒悒沉沉,日渐枯槁。母亲心疼儿子,百般开导,毫无用处,只得去劝父亲道:“樊家虽然穷,毕竟也算得上正经人家,跟那些市侩无赖不同。现在儿子一片心都在那女孩身上,我看是很难回心转意了。这样下去不是了局,不如改天我去访樊家太太,就便看看那女孩,倘若果真知书达理,人品不差,便许了儿子吧。”
父亲年近花甲,对这个独子亦是宠爱逾常,实在也不忍心看他这么日益消沉,只好喟然一声长叹,点头同意。
这天,母亲托词到黑帝祠烧香,路过樊家。「堂客」来访,照例由女眷招呼,少不得喊江城出来见礼。高母全神贯注等着,忽而眼前一亮,一个少女娉婷而出,明眸秀齿,娟妍无双,果然是万中无一的人物,当时便明白了儿子为何会那般神魂颠倒。待见她礼数周到,落落大方,实不愧书香人家的女儿,先前耿耿难释的那点门户成见,终于尽抛脑后。等江城进去,高母立即直道来意,说是希望结成姻亲;樊家本就认识高生,芝兰玉树,前途无量,当然是佳婿人选,这一下两家心同意合,皆大欢喜。
从「纳彩」、「问名」,到新娘子上轿进门,繁文缛节,总共消磨了一年多光景,高生早就盼得望眼欲穿,及至得偿心愿,自然把娇妻宠上了天,闺房之乐,如胶似漆。
然而好景不长,高生很快发现妻子的脾气有些乖张,有时莫名其妙生起气来,不但不受安慰,简直翻脸无情,把高生当作了仇人似的,什么恶毒话都能骂出口。
高生很有些迷茫,明明是仙女一般的姑娘,又是从小知书达理的,怎的竟会有如此暴躁的脾气?
迷茫归迷茫,江城的詈骂并不稍稍收敛。高生从小到大,何曾被人这样骂过?只是爱煞了这个姑娘,每每逆来顺受,当江城骂人时,总是好言安抚,不敢抗辩一辞。
为人子者需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因此按当时的习惯,婚娶之后多半不会分家。江城的骂声,有时直达公婆居所,二老听得又惊又急,私下找儿子问:“为何不拿丈夫的身份好好管束管束媳妇儿?”高生默然不语。
高生不肯说江城的坏话,江城却受不了了:“谁要那两个老不死的多管闲事!”
“你……你怎敢诟骂爹娘?”
这是高生第一次出言诘驳,江城大怒,抄起棍子便打,高生抱头窜出,“啪”,高生被关在了门外。他望着绝情的门板,呆呆地站在那里,想要上前叩门,却又不敢,他心想:“她总会消气的罢……”逡巡半晌,日渐西沉,及至星斗张满夜幕,那扇门始终紧紧关着。
翌日清晨,江城开门的时候看见了倚在檐下,抱膝而眠的丈夫,却并不觉得可怜,这天仍不许高生进门,高生为了求得妻子的原谅,长跪门前,直跪到腰腿无觉,而半日未进水米,头昏眼花,摇摇欲坠,猛听得一声悲啼:“儿啊!”高生听了这一声,全身陡地一松,向后便倒,给母亲扶住。江城只是冷笑,仿佛等着看一出戏似的,高母看看脸色蜡黄的儿子,恨声道:“他哪里对你不起,竟这样折磨他!”
江城冷冷道:“他自喜欢跪着,与我何干。”转身到内间去了。
这一来,高家忍无可忍,由二老做主,硬把江城撵回了娘家。总算高父顾及清门颜面,不愿事情闹大,并未诉讼离异。但清朝律例有「妻殴夫者,准予义绝」的解释,即,妻子殴打丈夫,可以按照「义绝」处理,也就是迫令妻子离开夫家,这在秦汉时叫作「大归」。义绝与休妻不同,不必去衙门办理手续,严格而言,算不得离异,只是相当于夫家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媳妇儿了。但倘若女家不肯,尽可以再上衙门诉讼,把「义绝」坐实成离异。
虽不似休妻难堪,女儿因为殴打丈夫被赶出家门,到底也是极不光彩,且极可能断送女儿身后的一件大事。樊先生既惊且惧,忙托人往高家说项,赔礼道歉,万望收回成命。高家二老当然不肯答应,两家就此绝交。
一岁春秋,匆匆而过。这天,高生百无聊赖,到市场上闲逛,打算拣几部书回家打发日子。正猫着腰在那里翻书,袖子给人一扯,转脸看去,却是前岳父樊先生。
“贤婿,”樊先生仍然用着这个称呼,脸上仿佛很自然的:“买书?走,我新得了一壶好茶,到舍下喝茶去。”不容分说,拉着高生就走。高生心中迷惘,明明该拒绝的,可是不知怎的,张不开这个嘴,于是身不由己地跟着进了樊家。一进家门,樊先生先深揖至地,行了个大礼:“小女顽劣不堪,都是老夫失于教导之过,连累贤婿受苦。”
高生忙还礼道:“伯父言重,折煞晚生了。她……这个,她还好么?”
樊先生扬声道:“江城!还不出来谢罪!”
门帷掀处,云开月明,高生拧过身子,眼睛便再也移不开去,一眨不眨地望着那暌别经年的妻子——她似乎清瘦多了,又似乎比从前更好看了些,她仍然戴着我送她的珥珰……
江城也怔怔看着高生,好像两年前窄巷邂逅时那样。看着看着,两人眼角都湿润了。
“来来来,”樊先生特别高兴:“今天你岳母蒸了鱼,需好好喝几杯。”
樊太太烧得菜肴很精致,但高生有些食不知味,心里惦着江城,耳边是樊先生殷勤的酬劝,一顿酒直喝到太阳落山,始而惊觉,不过已经醉的无法走路了。
“那就不要走了,”樊先生迷离着醉眼,拍拍高生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夫妻重逢,一夜缱绻,夙嫌泯然。第二天高生回到家,不敢以实情告父母,只道留宿在朋友家里。如此隔三差五跑一趟樊家,高家二老始终懵然不知。
樊先生看看功夫下得差不多了,这天径来拜谒高父,高父照旧挡驾不见,并令仆人传话过去说:“这是小两口事情,需犬子答应才好,你来求我有什么用处?”樊先生等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从容道:“请管家上禀高翁,贤婿早已和小女达成谅解,昨夜便是在舍下留宿。”高父闻言大惊,忙找来儿子一问,果真如是,勃然大怒道:“没出息的东西!十步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怎的骨头这样软,偏又去惹那祸水!”高生跪地俯首,一声不吭。高父一交坐到椅子里,仰天长叹道:“罢,罢,你的事情,你拿主意罢。”说话之间,樊家已经将女儿送来了,高父语声萧索道:“我们老夫老妻经不起折腾了,你们既已成家,不妨从此自立门户。樊翁,正好你在这里,便劳你作个见证,今日我们父子将分家的契约签了。”
高家只此一个独子,不似那人丁兴旺之家,昆季成年,早早的分配好祖产,因此,这算是一种很严厉的变相指责,虽不到断绝关系的地步,亦足以令人吃惊了。樊先生忙劝道:“父子一体,这又何必?高翁,此事万万不可。”但高父脾气极倔,自以为被儿子所辱,颇有心冷的意思,执意非分不可,最终分出一间别院给儿子,从此便算独门独户的两家人了。
接下来一个月,小夫妻相安无事,高家二老默默察伺,不禁欣慰,看来一年的反省,那姑娘终于悔过迁善了!没等高兴几天,但见儿子脸上,日日新增血痕,老两口相顾而惊,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恐怕将要故态复萌!
这天,二老正自用饭,忽闻惨叫声由远而近,高生惶惶然如一只被逐的兔子,抱着脑袋跌跌撞撞窜进来,躲到父亲身后。高父方待问时,只见江城满脸杀气地手持大棍直闯而入,当公婆二老不存在一样,拧起高生的耳朵往外便拖。高生大呼求饶,江城怒道:“吵什么!”一棍抽在膝盖上,高生痛的翻倒在地,那棍子便夹头夹脸地打落。高父见了,说不出话,气得几乎背过气去,将一根拐棍拄得笃笃作响,只是瞪着眼睛站不起身。高母看看老伴,看看儿子,不知先顾哪一边好,一面替老爷子顺着气,一面带着哭腔喊:“别打了,你要打死他了!”江城充耳不闻,又打了几棍子,这才在下人们惊惧的注视下悻悻离去。
“快,快请樊先生来!”高母拍着老伴的背心,大声吩咐,老伴的气总算顺了。
父亲的到来,似乎早在江城意料之内,因而父训谆谆,万般开谕,她一句都没听进耳朵。趁着樊先生缓口气的当儿,江城冷冰冰地开口了:“说完了么,说完就走吧。”
“你……你可不能再这样子怙恶不悛!”
“什么?”江城被这句话刺激到了:“你说谁恶?我自教训我的丈夫,干你何事?”
“你!”樊先生大怒,戟指江城道:“我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女儿!”
“那就当作没生过好了。”
樊先生给亲生女儿赶了出来,愤愤地找到高父道:“我管不来了,我没有这个女儿!我愧对你们高家!”丢下这么句话,拂衣而出,回到家后,一口气下不去,郁结成痞,不久便撒手人寰。樊太太听了丈夫的述说,泪如雨下,她原本身子不好,忧愤攻心,紧跟着亦随夫而去。然而江城仿佛被妖鬼附体,里里外外像换了个人,竟不回家奔丧祭吊,惟有每天殴辱丈夫。高生在家实在存身不住,又不敢去见父亲,只好偷偷向母亲求助。
母亲心想:本来出妻才是唯一的善策,可是老伴倔强,声明分居后,坚持不肯再过问儿子的家事;儿子又太懦弱,竟不敢写休书,为今之计,只有先找个地方让儿子避一避,徐徐筹谋。
高生独自住在母亲觅得的草舍里,有如逃亡的犯人,连门都不敢出,每天向隅至暮,凄清寂寞,煎熬无已。有一天实在闷得发慌时,看见东邻的李婆婆从窗外走过。此妪原操着牙婆、虔婆之类勾当,他喊了一声,唤到跟前,嘱托秘密找个姑娘来解解闷。
却说江城连日寻丈夫不到,这天无意听见一群妇人唠叨家长里短,说近日李婆婆常常带着陌生女子出入某间草舍,不知是谁家的汉子在偷腥?言者只当笑话,江城却格外留心,当天便到李婆婆家门前候着。
李婆婆向暮始归,老远看见江城由个丫头陪着,俏脸含煞坐在那里,不由得脸色大变,却又不能不硬着头皮上前,勉强笑道:“高少奶奶,怎么在这里坐?”
“正要问你,我丈夫在哪儿?”
“这……高少爷在哪里,老身怎么会知道?高少爷出门了么?”
“哼!”江城霍地站起,眼睛寒光暴射,犹如一对锋利的峨嵋刺,一步步逼到李婆婆跟前,森然道:“你最好老老实实地交代,姑娘或许能饶了你,若敢隐瞒,看我不拔光你这身老狗毛!”一把薅起李婆婆的发髻,伸脚在她膝弯一踹,李婆婆便跪了下去,惨叫道:“啊,啊!少奶奶饶命,我说!”于是将高生草舍所在,以及半个月来两次招妓之类诸般细节,清清楚楚的一一陈说。
“今天少爷吩咐,说从前在玉笥山见过一个姓陶的女子,一直惦记着,因托老身去打听。”
江城冷笑道:“那他现在软玉温香,正快活着了?”
“不不,”李婆婆唯恐再惹这头雌虎发怒,忙解释道:“那姓陶的女子虽然不贞,一时却不便在外留宿,因此并未随老身前来。”
听了这话,江城面色稍霁,唤丫头扶李婆婆起来。李婆婆如蒙大赦,忙不迭要走,江城道:“慢着!”李婆婆耸然止步,哆哆嗦嗦望着江城,眼睛里满是乞怜的神色。
江城略一思忖,道:“你带我过去,先灭了他的灯烛,告诉他那姓陶的来了。”说着举步便走,李婆婆不敢违拗,愁眉苦脸跟了上去。
到得草舍,李婆婆依令入内,悄悄说道:“高少爷,陶姑娘来啦!”一口气吹熄蜡烛,赶紧闪身出来,逃之夭夭。草舍顿时一片漆黑,高生隐约见一个身材高挑儿的女子纤腰轻摆,背着月光慢慢走来,按捺不住,抢上前去挽着她的手臂坐到床前,道:“陶姊姊,你总算来了,可想煞弟弟。”见那女子默不作声,还道她害臊,俯下身子便去摸她的脚,一面道:“自去年玉笥山上得睹姊姊的仙容,从此牵肠挂肚,念念不忘。”那女子却把脚一缩,仍然不说话。高生又道:“夙昔之愿,今日终于得偿,再让我好好瞧瞧你,成不成?”摸起火绒,点亮蜡烛,拿手掌护着火光移到那女子面前一照,只见江城脸若寒冰,正死死瞪着自己。
“啊!”高生一声惨叫,魂飞魄散,蜡烛“吧嗒”跌落,扑地跪倒,缩颈耸肩,仿佛绑上刑场将要杀头的犯人,全面失去了反抗能力,只等着江城处置。江城便老实不客气地提起丈夫耳朵,一路拖拽回家,往床下一推,高生滚倒在地,全身抖如筛糠。
这天晚上高生饱受了一种新花样的毒刑,两条腿被江城拿针刺得蜂窝也似,直折腾到四更时分方始罢手,却仍不许他上床。高生僵卧床下,熬过了出世以来最黑暗的一夜,从此愈发畏妻若虎狼,纵然江城偶尔因生理需要假以颜色,高生却始终怕得要死,更遑论行夫妻之礼了。江城大恨,一耳光扇下床去,污言恶语,极尽诋毁之所能。外人不明就里者或羡慕高生金屋藏娇,艳福不浅,只有他自己知道个中滋味,真是伴妻如伴虎,在家似坐牢。
略略了解高生苦况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同窗。这位王生也是个秀才,从祖上继承了一间精雅的酒肆,肆中多植红梅,一帮少年文士,常借此处相聚,折花买醉,赏梅赋诗。高生亦颇勤于此会,江城知道这是读书人的正常应酬,倒不怎么干涉。
一日,王生设宴相召,高生禀明妻子,终于征得了一天的自由时光,精神抖擞地赴那文酒之会。飞觞至暮,各人均有醉意,于是提议写条子叫姑娘。身为主人的王生首先叫好:“听说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间,名花倾城两相欢,不妨呼来共饮。”众人轰然赞同,于是羽笺飞传,各自吩咐随从小厮去招呼相熟的姑娘。一片热闹之中,高生默默离席,举步欲走。
“哪里去?”王生拽着他的衣袖,悄悄劝道:“不要扫大家的兴嘛,倾城之色,难道你就没兴趣领略领略?”
高生苦笑道:“不是小弟矫情,王兄,你知道我的苦衷,敝处妆阁里那位胭脂虎醋劲太大,实在无法应付,你就放我一马吧。”
王生笑道:“尊夫人耳朵再长,难道还能伸进我家?”使劲儿把高生按回座中。高生想想,自己确有些风声鹤唳了,于是努力坦然,看着莺莺燕燕陆续入席,举杯附众强笑。
未几,听得环佩叮咚,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娇形瘦影,盈盈而至。尚未入座,先拿那双俏伶伶的眼睛满场一瞧,座上众人无不色授魂与,连那些姑娘们都有我见犹怜之感,男子不消说。唯独高生心不在焉,与旁人格格不入。
那名妓阅人多少,一眼在人群中挑出了神色迥异的高生,再见他生的清逸俊朗,卓卓然拔乎其萃,不由有所属意,频频顾视。众好友见状,便开始起哄,拉着两人连肩并坐,那姑娘给众人挤兑地发赧,烟视媚行,更增三分楚楚之致,高生见了,亦不禁心动。
高生文才璀璨,以家中藏书宏富之故,涉猎甚博。那姑娘亦颇习诗赋,两人并头而语,姑娘感于高生胸中锦绣,不觉倾心,拉过高生的手掌,在手心写了个「宿」字。高生一惊而悟,仿佛大梦初醒,冷汗涔涔,美人恩重,固然不可辜负,但要他留宿不归,却哪里有这个胆量?一时心乱如麻,不知该去该留?反复权衡之际,梆子声响,已经是上更时分,座上酒客,纷纷把着相好的姑娘去觅温柔梦乡了,酒肆中变得稀稀落落,剩下的几人或者醉的厉害,伏案大睡,或者正对着姑娘下水磨功夫,成双成对喁喁私语。惟有末座一个美少年兀自在那儿对烛独酌,灼灼烛光映入点漆似的眸子,宛若秋江渔火。身边也没有姑娘相伴,只一个素衣小僮侍立在侧,清尚卓异,潇洒不群,见者莫不称奇。
高生亦觉好奇,只是隔得远了,醉眼朦胧,瞧不清那究竟是谁。
俄而,少年推杯罢饮,出门而去,那小僮却径向高生走来,道:“敝主人在外相候,请公子一语。”众人皆想:这人好不知趣,看不见高生坐拥美人么,这个当儿为什么请人家到外面说话?真是大煞风景!却见高生脸色惨变,踉跄起身,连向王生和身旁的名妓告别都顾不得,匆匆便去。
原来那小僮,正是江城的侍婢。
是夜,高生给吊在梁上,惨遭鞭笞。从此以后,江城的禁锢更加严格,不许他再迈出家门一步,至乎庆吊都绝,俨然软禁。而每每想起高生的不诚不忠,随时随地取棍便打,有时正在吃饭,忽然夺过高生的馒头,扔在地上,发狠地踩上几脚,再逼高生吃下,如此种种折磨,高生生不如死。
一日,城中大哗,据说不知哪里的得道高僧法驾降临,为大众说法。当天万人空巷,观者如堵,江城正在梳头,听见外面法螺法鼓之声震天动地,也顾不得盘髻子,握着头发就奔出去瞧。然而巷子口都挤满了人,简直插针不下,哪能看得见街上的场面?于是命丫头抬了椅子出来,站在上面踮脚引眺。当时女眷抛头露面,是件有伤体面的事情,像江城这样当众爬高,更简直不可思议,那是疯子、娼妓之流才会做的事情。因此她一站上椅子,人群中十个人倒有八个扭过头去看她的笑话,尤其闾里的流氓闲汉,见到江城的丽色,一个个兴奋不已,指指点点,大呼小叫。
法会阵容排场很大,僧侣、信士排成长长的队伍,络绎不绝,旌幢蔽日,梵呗喧天。忽而有好些人跪了下去,顶礼膜拜,一乘八抬檀舆徐徐而来,有人兴奋地叫道:“罗汉爷爷来啦!”跟着叩首不止。江城定睛一看,那檀舆中趺坐着一个白须白眉的老僧,眼睛紧闭,一动不动。江城心道:“这老头儿是死的活的?”心念一起,老僧仿佛有所感应似的,陡然张目,檀舆竟离开了直行的队伍,排开人群,径直抬到江城面前。
江城站在椅子上,茫然看着这老和尚,不知他跑到自己跟前做什么。老僧面无表情,说偈道:“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缩头去,勿使猫儿寻!”张口一道水箭,喷了江城一脸,胭脂粉黛,随水而化,流落满身。
人群大惊,不知这得道高僧「罗汉爷爷」为何竟起调戏女人来,有那认识江城的更是暗道不好,老和尚惹了母老虎,恐怕要挨打!一时间百口齐缄,所有人都望向江城,看她如何反应。
江城怔怔站在那里,好像着了魔一样,直到老僧的肩舆离开许久,才举起衣袖,擦一擦脸,迷迷惘惘地带着丫头自回家去。
高母趁着江城出门赶热闹,悄悄去探儿子,见高生坐在门槛上,骨瘦如柴,遍体鳞伤,忍不住抱住了大哭。高生亦哭,但不敢让母亲久留,高母一路哭回家,忧愁之甚,几乎打算轻生。这天夜里,她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一个陌生的老叟告诉她说:“不要烦忧,此是前世因果。江城原是静业上人所养的一只长生鼠,为你家公子的前世误杀,是以今生转世为人,特地寻高公子报杀身大仇。夙业纠缠,人力原不可解,今静业上人既为这段孽缘法驾亲临,必有回天之策,汝可以放心矣。”高母瞿然惊醒,懵懵懂懂,不知是真是幻?
就在高母惊醒的同时,睡在地上的高生也被唤醒了,他慌忙起身,熟练地找来尿盆,跪在床前伺候着。
良久,不见妻子反应,抬头一看,只见微微一点灯光中,江城泫然欲泣,轻轻摸一摸他的脸,把他拉进被窝。高生诚惶诚恐,不知好端端的让他进被窝做什么,必是又有什么酷刑,吓得四肢战栗,身子缩成一团。但觉江城一只小手温柔地摸了上来,摸到他满身的伤疤,低声啜泣道:“都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我……我好痛!”举手“啪”的一声,重重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泪雨涟涟道:“我真该就此死了!”“噼啪”连声,自己打个不停。
高生惊得呆了,一把抓住妻子的手道:“你、你怎么了?”江城不答,一头扎在他怀中嚎啕大哭,高生见这情形,手足无措,终于还是有些不忍,抚着妻子的头发,轻声安慰,问她何以哭泣?江城抽抽噎噎说起日间被老和尚吐了一身水,接着道:“那和尚必是菩萨化身,清水一洒,我心头仿佛有什么很烦恶的东西随之消失了。回忆昔日所为,好像上辈子的事情,我怎能那样恶毒!我简直不是人,我对不起爹娘,对不起你,对不起公婆,呜呜……”
高生也不清楚自己心中是何感想,他本非口讷之人,但积威之下,蜷伏太久,妻子虽遽然悔过,他倒不知该怎样答话了。
江城哭了半晌,渐渐平静下来,捧着高生的脸,絮絮款语,犹如久别重逢一般。这样谈了一整夜,翌日天尚未亮便起身收拾东西,要回到公婆那里,好晨昏侍奉问安。
高生早已养成了唯妻命是从的习惯,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折衣敛器,大包小包,由高生去叫门。高母出来一看,大吃一惊,不知儿媳又要搞什么花样,待听儿子叙述来意,欲待不信,江城已经带着丫头将行李什物拿进门了。
高父听见动静,拄杖来瞧,江城扑地跪倒,哀哀痛哭,乞求二老原谅。二老只求她不再折磨儿子便是上上大吉,哪里指望她能悔过求恕?不由面面相觑,高母道:“我儿何故如此,起来说话。”伸手扶起,江城绞着十根水葱似的指头垂首站在那里,好像新媳妇儿初进门似的,出不得声。于是由高生具道原委,高母想起昨夜的奇梦,方大悟而极喜,真是菩萨保佑!
此后岁月,江城顺孝膝下,以往的暴戾恣睢荡然无存,每见外人,腼腆如少女。有邻戚偶尔拿她从前种种“壮举”揶揄,则满脸通红,羞不可抑。如是三年,勤俭持家,家业骎骎日上,积下巨万财富。
这年高生乡试告捷,阖家大喜,江城趁机问高生:“当年在王生红梅酒肆中邂逅的姑娘,可还记得?”高生不知妻子何以有此一问,勾起了往日的一丝恐惧,嗫嚅不答。江城道:“我想替你讨个如夫人,你看如何?”高生有一个不打人骂人,待他温柔的江城,已经足矣,哪里敢奢望讨什么妾?江城见他不语,也就不再追问。
次年春,高生赴金陵应南闱会试,数月才返,一进家门,赫然见当日的酒肆名妓,正与江城庭前下棋,皓腕胜雪,交相辉映,一时呆若木鸡,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后来问起,才知道是江城动用私房钱,替那姑娘赎身脱籍。于是从此一鸾二凤,三宿双飞,逍遥天地。
这整件事的始末,都由那开酒店的王生细细说与蒲松龄得知,老蒲听完,神往不已。
“蒲兄,喂,蒲兄!回回神儿!想什么呢!”
“我在想,”蒲松龄望着天空:“既然那位神僧一口清水可以把悍妇化作绕指柔,为何不干脆拿这种水普降甘霖,洒遍大千世界,好拯救深受家暴之苦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