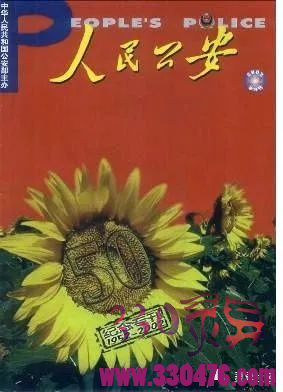安徽青阳旧时有座「十王殿」,里面供奉着十殿阎罗。十位阎罗王率领座下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及各种幽冥鬼神星罗林立,济济一堂。殿内长年燃着几支昏暗的素烛,将本就栩栩如生的鬼神木雕,更映的鬼气森森。此殿周遭数里,鸟雀不落,虫蚁不生,夏日入内,犹自阴风彻骨,有时夜里庙廊之下,隐隐可闻凄厉的拷问惨嚎,令人毛骨悚然,除了庙祝和特别虔诚的信徒,轻易无人敢近。当地传说,都是当初造像的匠人手艺太高明,把神像造得过于逼真,以致于木像年久通灵,无形中将幽冥鬼气,连通到了人间。
青阳县有个书生,姓朱,字小明,二十多岁,天生落拓不羁,尤其嗜酒,颇有些李太白、阮步兵的狂士味道。不过文才却比李白、阮籍差的太远,勉勉强强混上个秀才,就此科场困顿,裹足难前了。
一日文人结社,论文联诗之后,始而饮酒。朱小明来趁这种文酒之会,主要就是冲着喝酒来的,酒菜一上,方才切磋文章时那副愁眉苦脸,立时舒展开来,纵酒雄辩,谈笑风生。众同案看得有趣,纷纷拿话揶揄他,朱小明也不放在心上,随口应付,酒到杯干。待喝到七分醉意时,一同案忽道:“小明兄旷达豪迈,委实令人心折,不过有件事情,我猜以小明兄的胆气,恐怕也是不敢尝试的。”
朱小明醉眼斜睨道:“你不必激我,什么事情,且说来听听?”
那位同案指着斜挂树梢的一钩残月道:“眼下月色正好,小明兄敢不敢到十王殿中,将东庑下那尊碧面判官请来,大家同酹一杯水酒,好祝祷我等来年闱战顺遂?”
朱小明道:“我干什么好端端放着酒不喝,却替你去跑这个腿儿?”
同案笑道:“想喝酒嘛,容易得很,小明兄若能请得判官来,我们便特地为兄置一席盛筵,又有何难?”众人听了,纷纷鼓噪叫好。朱小明大喜,晃悠悠站起身道:“诸位既有此雅兴,小弟走上一遭又何妨?不过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若请得来判官,你们可不许抵赖。”众人大笑,连称不会,见朱小明趔趄而出,都不信他真敢夜闯那百鬼群集的十王殿。
等了一会儿,不见朱小明回来,有人道:“朱大胆约莫已经逃回家了,我们也该散了罢。”有几人便起身告辞,忽听一声长啸由远而近,轰隆大响,大门撞开,朱小明扛着判官木像歪歪斜斜走进来,望食几上一放,先在神像前酹下三杯酒,打了个躬,转身道:“判官到了,谁要祝祷赶紧请吧。”
众人原是同他开玩笑,谁曾料到他居然真把神像扛了回来。烛火摇摇,那判官绿面赤髯,居高临下,一双巨眼仿佛射出光芒,俯视着众人,将一个文士雅集,硬生生变成了冥司鬼衙。众人恍惚都觉得自己已经身入阴世,即将被判官问罪,投入刀山油锅、无边地狱,无不毛发森竖,一时间鸦雀无声。
“怎么,”朱小明皱着眉头道:“诸位心既不诚,何苦支使小弟跑这一趟?神仙我请来了,明天的酒,你们可赖不得。”
“不赖,一定不赖!”那同案小心赔话道:“我们是服了朱兄的胆力了,还是劳驾送神归位吧。”
朱小明见众人噤若寒蝉的可怜样,暗暗好笑,又寻思,十王殿远的很,一去一回需费不少力气,不如就近扛回家,几时得空再送神归位便了。于是洒下一杯酒,向那神像祝道:“寒舍匪遥,狂生洁觞置酒,斗胆奉请尊神移驾小酌,幸勿怪罪。”合十一礼,负起而去。

第二天,众秀才如约请客,专请朱小明一。昨夜一役,众人真有些忌惮这个愣头青了,没人敢再像往常一样大开他的玩笑。朱小明给群星拱月般恭维的通体舒泰,直喝道日暮时分,才半醉而归。回到家酒兴未阑,继续挑灯独酌。忽然门帘一掀,一个青面赤髯,身形高大的怪人长驱直入。朱小明扭头看去,大吃一惊:这不是我扛回来那尊判官么!
判官来到几前,拱拱手道:“承蒙高义相订,今夜恰好有暇,不揣冒昧,特来践约,叨扰,叨扰。”
判官竟然真的活了过来,陪我喝酒!朱小明大喜,也不顾忌什么人神之防,一把拉住判官的袖子,拽着他落座,自去洗盏、添炭、烧水。
“不必劳动,”判官远远道:“天气尚暖,冷饮即可。”
朱小明也就不再客气,替判官斟满酒,匆匆转入内室,喊他妻子:“夫人,家里还有什么吃的?赶紧弄两个好菜,我有贵客。”
“贵客?谁呀?”
朱小明略加踌躇,还是将昨夜如何打赌,如何在神像前祝祷,如何扛了神像回来云云,要言不烦的说了一遍。
一番话把妻子吓得脸色惨白,死死拖着丈夫的手,不让他出去。
“这是干什么,人家找我喝个酒而已,没有恶意的。”朱小明好劝歹劝,终究安抚了妻子,可是妻子已经受惊不轻,只好自己弄了两个冷碟,卤三件、盐笋干,端出去同判官把杯痛饮。
两杯下肚,展问姓名,判官道:“姓陆,前世有名,如今阴司当职,没有名字。”
人鬼殊途,却该谈些什么?朱小明又试探着问些人间常聊的话题,风月新闻、史实典故,陆判官竟毫不陌生,二人谈古论今,渐渐谈到当前,谈及科举,最后朱小明付诸一声长叹:“怀才尚且未必可遇,何况在下樗栎庸材,恐怕此生难有出头之日。”
陆判道:“朱兄毋庸沮丧,烦赐芳翰一览。”
朱小明大奇,难道阴司判官,也能读人世的八股文?到书房找来两篇新作的窗稿,陆判看了,未置一辞,淡淡的放在一旁,继续喝酒。
朱小明已喝了整整一日,酒量虽豪,也终究禁受不起,最后自己也不知何时醉倒过去。待醒来时,残烛昏黄,曙色当窗,陆判已经离开。拿过那两篇窗稿一看,满纸批删,被改得面目全非,不禁赧然,看来那位鬼客不但看得懂人间八股文,而且造诣颇深,不知以后有没有机会向他请教?
当天晚上,朱小明便等到了答案,陆判带了一坛好酒,一提佳肴,乘风而至。两人大快朵颐,言谈更加投契,夜里干脆抵足而卧,共话至深更。从此陆判三天两头往朱家跑,胡吃海侃,有时也指点指点朱小明的文章,时间一久,朱夫人也不再害怕这位职掌亡灵罪业的幽冥判官了,只拿他当丈夫一个普通朋友。
这天晚上,朱小明躺在床上,瞧着陆判自斟自饮,未谈得几句,挡不住倦意潮涌,沉沉入眠。忽觉胸腹间一阵微痛,惊醒过来,只见一灯如豆,床沿插着一把蓝汪汪的匕首,陆判端坐床前,眼睛射出狼一般碧绿的光芒,满手血迹,正慢慢捋着一条肠子。
这是干什么?朱小明心头猛地一寒,低头看去,自己整个胸腹被纵向剖开,脏腑毕露,肠子溢出体外,不消说,陆判手里捋的是自己的肠子!
“陆兄!”朱小明赫然发现自己竟还能开口说话,而声音已带了哭腔:“无怨无仇,你、你为何要杀我?”
“哈哈哈,”陆判大笑道:“别怕,别怕,我怎么会杀你,我是在替你换一颗慧心。”
什么?
朱小明举手想摸,陆判叱道:“不要动!”将捋好的一盘肠子塞回腹中,揪起切开的皮肉对齐缝合了,拿朱夫人的裹脚布在他身上裹了几圈,拍手道:“好了!”
朱小明唯觉身子有些发麻,倒并无痛楚,斜眼一看,床上也不见血迹,床前小几上放着一块拳头大的肉。
“这就是你的心,”陆判拿起那肉块给他看:“你瞧,心窍闭塞,是故文思不敏。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冥界留意,刚刚终于等到一枚上乘的慧心,赶紧拿来替你换上。”
朱小明一时未能从震骇中回过神来,哑口无言。陆判拿起心脏道:“你的这颗心,我还要拿去补缺,你安心睡罢,明日便可大好了。”
朱小明胆子再大,这一夜却如何睡得着?次日清晨对着天光一看,胸腹正中一道淡绯如线,直至肚脐,除此之外,全无异状。
难道真的换了一颗心?
他手扪胸口,抽出自己前日未完的一篇窗课,忽然思如泉涌,仿佛平生读过的所有文字,自行排列成章,急欲喷薄而出,忙将那残稿丢到一旁,援笔疾书,如阪上走丸,一气呵成,搁笔披览,不由惊得呆了,这竟是我的手笔?!
隔天陆判复来,朱小明忙呈上新作,陆判颔首道:“如此笔力,乡试夺魁足矣,只是你禄命有限,注定不能大富大贵,更进一步,此乃命数,我也爱莫能助。”
朱小明倒不在乎什么大富大贵,但求能乡试中举,则此生无憾。未几秋闱应试,果然一举夺得解元,众同窗莫不诧为奇事,都说朱小明中举已经万万不可思议,更不用说高中解元了,难道那试官瞎了眼睛?及见到朱之闱墨,始相顾而惊,各叹弗如,当真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从出榜报捷开始,朱家贺客盈门,一直热闹了十几天方休。这天晚上,待客人散尽,陆判才现身贺喜,朱小明笑道:“唐人有泰山之力,小弟能有今日,全仰仗大哥之力。”拉着陆判坐下喝酒,两人心情舒畅,不觉喝得舌头都大了,朱小明道:“易心伐髓,受惠已然良多,不过小弟还有一事,求大哥帮忙。”
陆判道:“你我兄弟,何必客气,但说无妨。”
“嘿嘿,”朱小明促狭一笑,道:“我在想,既然心肠可易,想必面目容貌也可以更换?”
“自然可以,兄弟想换一张什么模样的脸?”
“不是我,是内人。”朱小明喷着酒气,低声道:“实不相瞒,拙荆身材不恶,房中的功夫亦甚了得,就是那张脸不够漂亮,不免有些狐裘羔袖之憾,白璧微瑕之疵。我想有劳大哥,给换一副娇媚容貌,想来内人亦会欣然。”
陆判纵声大笑,一部赤色长髯吹得笔直,拍着朱小明道:“兄弟真是妙人。这事容易,包在我身上,待我仔细觅一张绝色容颜来。”
这件事交代过后,陆判一连数日不曾再来。一天半夜,朱小明好梦正酣,忽然给人拍醒,睁眼一看,入目就是陆判那双碧彤彤的夜眼,忙起身跟他来到前厅。陆判取出个圆圆的包袱,说道:“近日没有什么佳丽丧命,我等了多日,终于才等到这一个。”说着打开包袱,朱小明移烛凑近,只见一个长发人头,血迹未干,也看不出是丑是妍。陆判道:“不必看了,包管是个美人。事不宜迟,立即开始吧。”
两人来到卧室,朱夫人正脸孔向内,侧身而睡。陆判将人头交给朱小明抱着,从靴页子里拔出那把清光流动的匕首,按着朱夫人的脑袋,像切豆腐似的,一刀下去,“嗤”的把头切了下来,接过那美女的首级合在断颈之上,上下左右细细对准了,用力按了几按,拿一只枕头塞进朱夫人颈下,托着头颈嫁接之处。
朱小明站在一旁,看得冷汗涔涔,生怕陆判一个失手,竟把妻子弄死了,岂不是追悔不及?可是陆判动作太快,不等他叫停,手术已经完成,回首见他抱着人头呆立着出神,低声道:“快去找个偏僻处深埋了,切莫让人看见!”
朱夫人醒的比往常早些,她觉得脖子不大舒服,似乎有些发麻,又似乎有点发僵,以为是睡落了枕。揭被而起,举手一捏,干结的血迹簌簌而下。朱夫人大骇,一声尖叫,房外侍候的丫头赶紧奔进来,看见了夫人,惊得挪不动脚。
“夫人!”那丫头眼睛发直,战战兢兢举手指着道:“你脸上好多血!”
“快,快打盆水来!”
丫头忙去打了一盆水,朱夫人到处乱摸,可是并无哪里疼痛,不知血从何处流出?及至一盆清水洗成了鲜红,丫头递上面巾时,猛地看见朱夫人的模样,吓得向后一躲,面巾掉在了地上。
“怎么回事!”朱夫人叱道:“见鬼了吗!”
“夫人,你的脸……你的样子……”
朱夫人还道自己的脸破了皮,忙抓起妆台上镜子一照,只见镜中人长眉掩鬓,艳光摄人,娇怯怯的眼睛中透着三分奇,三分惊,三分惧,还有一分喜。
这是谁!
朱夫人触电似的甩手丢了镜子,瞪大眼睛看着丫头,主婢二人相顾茫然。朱小明蓦地推门而入,见了此情此景,忍不住大笑道:“「行人咸息驾,争拟洛川神」!夫人,你现在真有倾城倾国之姿,我这藏娇金屋的关防,可要再严密些才妥当。”
朱夫人哪有心思开玩笑,拉住丈夫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是……是陆大哥搞的鬼?”
朱小明笑道:“夫人聪敏,什么都瞒不过夫人。”拉下夫人的衣领,只见一丝极细的淡红痕迹环绕颈上,上下肤色,判然迥异。
虽说“金屋藏娇,严密关防”,但朱家娘子一夕之间面目全非,实在太过惊世骇俗,“换头”之说,传为奇闻,不胫而走,一时轰动江淮。众口究诘,朱小明敷衍不掉,只好推说夫人梦见头颅被换,一觉醒来便已如此,至于究竟是什么缘故,他们夫妻俩也搞不清楚。
就在流言纷扰之际,一天有客人来访,名帖递进来一看,姓吴,是一位致仕还乡的监察御史。朱小明不识此人,不知他来找自己有什么事?肃入落座,只见这位吴老爷子一脸的焦灼之色,寒暄未毕,就忍不住站起来道:“老朽冒昧叨扰,是有一事相求。”
朱小明道:“前辈有什么吩咐?”
吴老爷子道:“言重,老朽想见一见尊夫人。”
生客来访,居然指明要见人家的内眷,这在当时是极不合礼数的行为。但朱小明看他坐立不安的模样,似乎是有什么迫切需要索解的隐衷,因而指使听差,去唤夫人出来。
朱夫人自然很不高兴,心里埋怨丈夫冒失,怎能让我抛头露面去见一个生客?到得客厅,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站在椅前,失魂落魄地盯着自己,更感不悦,不过还是在丈夫的介绍下,上前请安见礼。
“你……”吴老爷子声音沙哑了:“你当真是,他的夫人?”
朱夫人奇道:“是的,这位是拙夫。”
“那么,换头之说,看来是真的了。”吴老爷子倏然转身,劈手抓住朱小明的肩头,暴喝道:“你是用什么邪术,杀了我女儿!”
朱小明错愕道:“你说什么?”
吴老爷子指着朱夫人怒道:“这是我女儿的头脸!你这无耻的好色之徒,杀了我女儿,却用邪术夺她的头颅换给了你浑家!士林中竟出了你这等丧尽天良的畜生!我、我一定奏明皇上,将你千刀万剐!”说到极怒时,涕泪纵横,又愤愤看了朱夫人一眼,拂衣而去,留下朱氏夫妇面面相觑。
原来这位吴御史年近花甲,膝下只得一个女儿,爱逾掌珠。此女生有国色,早早订下了姻亲,谁知没等出嫁,男方突然得急病死了;后来又订下一门亲事,六礼未毕,男方竟又死掉了。这样一来,姑娘的名誉不免受到些影响,所以直到十九岁,仍然没有出阁。
每年上元灯节,十王殿都有迎神赛会。平时游客绝迹的“鬼庙”,迎来了一年中难得的热闹,尤其晚间灯会,各色花灯琳琅满目,当真是夜花千放,鱼龙飞舞。每到这个时候,向来不轻易出门的大家闺秀,也会被暂时解除禁足,在长辈或佣人的保护下,出来感受真实的烟火人间。
庙会上百业齐集,薰莸杂处,下九流的江湖无赖也最多。吴小姐丽质无双,才一现身,立刻被一个采花贼盯上,暗中跟了一路,探明了闺阁所在。第二天夜里,便翻墙潜入吴家,别开绣房房门,迎面撞见一个丫鬟,一刀刺死,踹开一旁,又去逼奸吴小姐。吴小姐抵死挣扎,拼命大叫,那采花贼竟按之不住。眼看前进灯火亮起,已经惊动了吴家人,而自己“好事”未遂,不由恼羞成怒,一刀捅进吴小姐脖颈,犹不解恨,踏住了尸体,用那把解腕尖刀生生把头割了下来,掷在床下,才逾墙逃去。
吴夫人掌火来看,见一地血泊,女儿头颅在地,尸身横床,当时便昏了过去。服侍的丫头惨声尖叫,惊得举家尽起,赶来一看,都吓得呆在门前,不知所措。好容易收拾心魂,抬了小姐的尸体出来,停在堂上,满门啼号,吴御史和夫人几次哭到晕厥。
哭了一夜,吴家上下精疲力尽,待要打发人报官时,却发现小姐的头不见了。
昨晚明明已将尸首拼合,怎会不见?吴御史大怒,怪下人监护不周,致被野狗叼走,将一干下人重重责打,跟着越过青阳县,直接将案子报到了池州府衙。
吴御史翰林前辈,本地缙绅,十几年监察御史生涯,朝中大佬,多是故交,知府岂敢怠慢,当即交代下去,限期捉拿凶犯归案。
一晃三个月过去,凶手仍未落网,而朱夫人换头奇闻,倒是渐渐传进了吴家的耳朵。
本来凶手未擒,大仇未报,女儿死不瞑目,人家换头也好,换脚也好,吴家哪有心思理会这些闲事?可是来报告的人越来越多,都说那位朱夫人换的头,就是吴小姐的。
众口一词,况且有熟识的人声称亲眼见过那位朱夫人,一定不会看错,吴御史不禁起了疑心,想起古人志怪的种种传说,难道上苍显灵,让女儿复活了?为此剖开棺木一看,棺中仍然只有一具无头尸体。
衙门迟迟不能破案,吴御史再也按捺不住,决定亲眼去看个究竟。及见朱夫人的容貌与女儿一模一样,悲愤交加,当时就忍不住要把朱小明碎尸万段,一离朱家,径往府衙诉讼。
被告朱小明传唤到案,仍然坚持从前的说法,说妻子的头是换自梦中,杀人云云,绝无其事。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知府难以委决,而朱小明是本州乡试解元,不能对他随意用刑,连拘禁都拘不得,他既不肯承认,又没有真凭实据,只好放他回家。
朱小明却已经打听清楚了吴御史家门惨案,不免心生愧意,人虽不是他杀,但害的人家姑娘尸首不全,岂不是造孽?这天晚上,待陆判一到,说起此事,问他有没有什么补救之道?
“人死复生,断无可能。”陆判夹着一条臭鳜鱼,吃得咂咂有声:“不过,补救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而且还能解你眼前困厄。”
“愿闻其详!”
陆判道:“我使个法子,令吴家父女见一面,吴小姐自会揭发凶手,我再叫她替你开脱两句便了。”
“你不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如何见面?”
“自然是在梦里相见。”陆判擦擦沾在胡子上的汤渍,站起来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办。”
自女儿惨死,吴家二老不知已梦见过多少次爱女的幻影,可是哪一次都不及今夜的真实。
“女儿蒙陆判官照拂,万幸能再见爹娘最后一面。”吴小姐跪在无尽黑暗的一点光芒里,凄然道:“爹娘在上,容女儿细禀:杀害女儿的凶手,是苏溪人杨大年,与朱相公无干。朱相公只为不满夫人容貌,托陆判官取女儿首级相易,女儿因此得以身死而头生,得以……留一点血肉与爹娘相见。爹娘若是想念女儿了,便去看看朱夫人……”说到这里,泣不成声,二老心疼不已,举步上前,要把女儿搂进怀里时,那点光芒却逐渐为浓重的黑暗吞没,声音亦变得缥缈遥远,只听一声“爹娘万万保重”,眼前漆黑一片,登时惊醒。
吴御史大睁着眼睛看向夫人,夫人也大睁着眼睛望着他,原来两人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女儿遗魂不昧,显灵入梦了!
二老既伤心,亦感动。次日一早,吴御史跨马直奔府衙,找到管户籍的书办一查,果然有个叫杨大年的,恳请知府提审。公差上门,杨大年做贼心虚,还以为事情败露,拘捕反抗,这一下不打自招,被公差暴打一顿械入衙门的时候,早已遍体鳞伤气沮神丧,略加勘问,便即招认伏罪。
案子终于水落石出,凶手杨大年秋决问斩,朱小明洗脱了邪术杀人的嫌疑。一天,吴御史再次登门拜访,他这次来,第一是为了致歉,另外还有第二个目的,说起来却有些忸怩。
“朱老弟,”他说:“这个,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能否……能否再请尊夫人出来坐一坐?”
朱小明笑了一下,继而端正神色道:“老前辈,晚生也有个不情之请:倘蒙不弃鄙陋,我想让拙荆认你老作干爹,下半辈子,就由我夫妻二人侍奉你老人家。”
吴御史呆住了,跟着眼圈泛红,忙把头垂下去,泪水止不住簌簌滴落。他原本的心愿,不过偶尔看一看亡女容颜,同女儿的“替身”说两句话,已是莫大的安慰,只因素无交情,连这样一点心愿也恐怕所望过奢,哪里敢指望再为人父,看着女儿的脸,听“她”喊一声爹娘?他喉头哽咽,说不出话,只有紧紧抓着朱小明的手,用手掌的温度感激他,为自己颓唐黑暗的晚景带来的新希望。
朱夫人的头颅,缝在吴小姐的身体上,使这位不幸而殇的蓓蕾得以全尸殓葬。朱氏夫妇亦不负所诺,一力挑起了吴家二老的晚年。
三十载春秋就在平淡的朝朝暮暮中匆匆流过,期间朱小明三入春闱,皆无功而返,知道自己命中功名止此,也就不再强求了。
一夜陆判到来,同他说道:“兄弟,你听了这话,切莫伤心,我昨日查知,你的阳寿行将耗尽了。”
朱小明本是豁达之人,听了这话,也不曾如何动容,只淡淡问道:“是了,我还有几天可活?”
“五天。”
“大哥既这般说,想来亦没有法子相救。”
陆判摇头道:“生死皆出天命,休说愚兄,就是十殿阎罗,亦无能为力。况且生死无非阴阳之别,生又何欢,死又何苦,不必恋生而畏死。”
朱小明道:“有大哥照拂,我自然不怕。”于是从容交代后事,五日而死。
第二天成殓之后,朱夫人搂着五岁的儿子,扶着灵柩放声痛哭,忽听朱小明的声音道:“不要哭了,又非永诀,何必悲伤至此。”朱夫人抬头一看,丈夫好端端站在灵前,伸手要来搀他。
朱夫人大骇,搂着儿子往后一缩,儿子却认得父亲,挣开母亲扑到爹爹怀里。朱小明抱起儿子道:“陆大哥说生死一体,果然如是,你看,我今已成鬼,倒跟人也没什么分别。”
夫人这才惧怖尽去,惊喜道:“古有还魂之说,老爷既然有灵,何不再生?”
朱小明道:“天命不可违,何况虽死如生,并不妨碍咱们一家相见,不必去动那个心思了。”
夫人毕竟还是痛心,关切地看着丈夫的脸道:“老爷在‘那边’,可……一切还好么?”
朱小明笑道:“有陆大哥在,怕什么,大哥举荐我在阴司做些文书勾当,与寻常小鬼不同,因而一无所苦,夫人尽管放心,不要胡思乱想。”
朱夫人还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生怕眨眼之间丈夫又没了,朱小明却不容她絮语,看看外面道:“大哥还在外间,有什么吃的没有?”
“有,有!”朱夫人见丈夫还能用人间烟火,越发高兴:“我去热菜。”擦干眼角的泪痕,指挥下人置酒治菜,但听得饭厅中欢声笑语,哥俩雄辩高论,一如生前,直到夜半方歇,进门一看,满桌杯盏狼藉,二人已杳然无踪。
此后朱小明每两三天回家一趟,有时也在家过夜,就便料理一些家务,含饴弄儿,灯下教读,更不在话下。儿子资质极好,九岁能文,十五岁进学,一直以来,竟不知父亲其实已殁。
这年中秋,一家三口喝过团圆酒,朱小明望着中天明月道:“人有离合,月有圆缺,明天我就要走了。”
母子俩均感愕然,朱夫人道:“走去哪里?”
朱小明道:“天帝委任我为太华卿,明日一早,我就要远赴华山,今后山水阻阔,不能再像这样时常回家了。”
母子闻言大惊,失声痛哭,朱小明安慰妻子道:“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鸾凤,儿子已经成人,家中生计,我也可以放心,你不要太痴了。”再摸摸儿子的头道:“雏凤清声,你将来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好好做人,好好孝敬你母亲,十年之后,我们父子还有再见的机会。”说完径出门去,冉冉消失于月色中。
朱公子的科运,果然较乃父更上层楼,进士及第,二十五岁擢行人司司正,职司颁行诏敕、抚辑四方,以及代君上祭祀山川。
这年,奉旨祭祀西岳华山,行经华阴,忽有一队车马迎面驰来,见了朝廷仪仗,竟不回避。朱公子大奇,什么人敢如此猖狂?打马上前一看,车中坐的,赫然是十年未见的父亲,忙拦在车前,伏道大哭。朱小明令御者勒停车马,温言道:“你很好,你很好,有子如此,我可以瞑目了。”儿子越发嚎啕,朱小明叹道:“痴儿,痴儿。”解下一把佩刀,递给儿子道:“此刀佩戴左右,可佑你富贵平安。”说罢叩辕而去。朱公子起身欲追,父亲的舆马人从飘忽若风,瞬息远逝,眨眼的功夫已消失不见。他怔然良久,抽刀出鞘,寒光射目,只见刀身镌有一行小字:「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朱公子始终凛遵此训,胆大心细,圆融清正,果然一生平安,官至兵部侍郎。他门丁兴旺,生有五子,以「潜龙勿用」之韬,分别取名沉、潜、沕、浑、深。一夜父亲入梦,嘱咐道:“老四朱浑,可传此刀。”朱公子依命行事,朱浑后来做到左都御史,总掌台宪,清刚不阿,为一代贤臣。
蒲松龄《聊斋志异·陆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