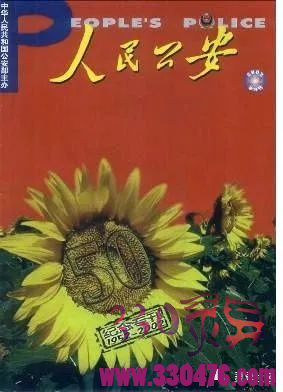从前,顺天府有一户姓马的人家,世代喜欢莳花,尤其爱菊成癖。这一代当家人马子才更是个菊痴,他的宅邸周围,房前屋后,庭院园圃,但凡宜栽之壤,满眼亭菊,不知种了几千几百本,而他犹未满足,只要听说何处有什么名种佳品,哪怕千里迢迢,也必亲自跑上一趟,百般求购,不惜一掷百金而后快。
马家原非钟鼎豪门,马子才又事事学陶渊明,清高自许,不屑营营,他自己多方购菊,却不许人家来买他的菊花,因为「松菊傲骨」——要保持气节,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因而境况越来越不景气。
境况不好,爱菊之癖却深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天有个金陵来的过客借住在马家,见马子才爱菊,便谈起他金陵一位表亲亦好此道,而且颇有几株异葩,为北方所无。马子才听得心动不已,待那客人勾当事了,便随之南下,一径来到金陵城,如愿买得两株异种花苗,如获至宝,恨不得插翅飞回家,立刻开始栽培。
路上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路形单影只,不比南下时有人相伴,格外显得漫长。马子才跨在驴子上慢吞吞走着,百无聊赖,忽听得身后勒勒声响,回头一看,一部精致的「油壁车」悠悠驶来,车篷四周幔幕低垂,不问可知,内中乘着女眷。车左一个少年,也跨着头青驴,丰姿洒落,顾盼炜如,一双眼睛亮如天星,在这滚滚浊尘之中,好似寒山明玉。马子才见了,不禁赞叹道:“好一个油壁车轻郎马骢!”
那少年听见,爽朗一笑,“嘚嘚”赶将上来,并辔寒暄。二人互道姓名,少年自称姓陶,车中坐的,倒不是恋人,而是胞姊,只为姊姊厌居金陵,送她赴北方觅地卜居。
马子才也自告行止,那少年听了,眼睛越发明亮,笑道:“不想在此愁旅之中,竟能邂逅先生这等举世无双的雅人,千里市菊,足为佳话。”马子才谦逊了几句,聊不多时,渐渐聊起金陵的菊花,少年侃侃而谈,竟然深谙艺菊之道。这次轮到马子才眼睛发亮了:“足下所论,精辟新颖,真令人心悦诚服。倘蒙不弃,请往敝处盘桓几日,容乡愚朝夕请益。”
少年忙称言重,又道:“先生的乡里若有容居之处,小弟也很想同先生作个邻居。”
“怎么没有,”马子才忙道:“在下就刚好有一所空房,虽不甚轩敞,倒还清净,令姊既未有定止,不妨便去看一看。”
于是少年去同姊姊商量,马子才瞥眼而视,见帘幕半启,露出一张晶莹的俏脸,心中剧震:“真天下绝色也!”有顷,少年策骑而回,说道:“家姊的意思,房屋窄小不要紧,院子最好能宽敞些。”
马子才忙道:“有,有大院子。”
马家的空房,毗邻马宅之南,只三四间小室,但院落极大,陶家姊弟十分满意,就此租住下来。少年每天寻马子才喝酒,就便替他打理打理菊花,此人果然是莳花高手,竟有办法令已经萎谢的花儿起死重生。马子才大喜,心想此子既擅种菊,巧的是也姓陶,难道真是陶渊明的族嗣?二人情投意合,感情日深,马子才便拿少年当亲兄弟般相待。
「官客」过从亲密,「堂客」便也容易合得拢。马太太心细,见少年每天同丈夫看花饮酒,料想是没有正经营生的,便时常带些柴米蛋蔬去看陶家姊姊,见她天仙般的人物,温柔娴雅,毫无半分轻佻,亦不觉钟爱,通问闺名,说小字叫作“黄英”。
“英妹妹,”马太太看着帮她做针线的黄英问道:“你这样的相貌人品,怎的仍然是一个人?”
黄英知道这问的是婚事,不禁赧然道:“时候未到。”
马太太心想:“姑娘该有二十岁了罢,早该嫁了,怎么说时候未到?”打趣道:“想来这杯喜酒不远了?”
黄英低声道:“尚有四十三个月呢。”
“什么四十三个月?”
黄英抬眼看了马太太一眼,美目泛出奇光,欲言又止,把话头引到别处去了。
马家原本已经不甚宽裕,又要照拂陶家姊弟,用度益发紧张。少年看在眼里,一天同马子才饮酒时,突然道:“小弟叨拢马兄实在太多,令人好生过意不去,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明日开始,小弟打算卖菊花谋生。”
“什么?你要卖菊花?”
“是的。”
……
马子才默然半晌,道:“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若艺菊只为沽名图利,岂不折辱了此花的气节。”
少年笑道:“大哥所论不免过迂,倘使君子能够不穷,当然还是不穷好,何况种花卖花,此乃雅事,而自食其力,有何不可。”
马子才深不以为然,停杯不语,两人话不投机,少年讨了个没趣,怏怏地走了。
第二天,少年又到花圃中,将马子才扔掉的残枝劣种尽捡了去,由于昨日的龃龉,马子才不好意思开口问他捡这些死花做什么,他也不说。当天马子才照常置下酒菜,少年却不曾来。打这天以后,少年几乎绝足于马家,只偶尔来喝过两次酒,略略勾留,旋即匆匆离去。
转眼时届初秋,菊花次第开放,马子才越发忙碌,每天早起巡看菊园。清晨推门而出,忽听得院外陶氏姊弟居处人声喧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赶去一看,只见乌泱泱一片人,也有赶着牲口的,也有赶着车的,也有负着袋子的,人头攒动,都拥在陶家门前,高声嚷嚷着争着买花。马子才心想:“那小子不过捡了些我不要的枯枝栽培,又没有什么名种佳卉,何至于挤得人山人海的抢购?”一念方歇,人群中挤出一人,手捧一本「天孙锦」,满脸兴奋,大呼小叫地去了。接着不断有人骑马驾车而至,亦不断有人捧了花出来,皆是极其罕见、甚或从未见过的异种,引得外围的人群艳羡不已,越发拼了命地往前挤。
马子才看得反感而愤懑:“枉你也姓陶,竟大开门户,折菊贩沽,你先祖陶渊明的高洁风骨,可算扫地而尽了!”唉声叹气,顿顿脚便想走,然而眼睛却为那层出不穷的奇种神品吸引,挪不开去。他愈看愈奇,愈看愈惊,陶家到底种了多少神异的奇葩?想着想着,两只脚由不得自己,快步绕到陶居宅后,嘭嘭嘭地叩打后门。
打了半晌,那少年笑嘻嘻地探出身子,将他迎了进去。一进得门,入目便是一幅巨大无朋的地毯,定睛再看,原来全是菊花!从前的半亩荒庭已尽数化作菊畦,珠铺翠绣,万紫千红,除房舍之外,整个宅院几乎没有一尺空地,马子才看得合不拢嘴,呐呐道:“贤弟,你……你哪里来的这许多异种?”
少年笑道:“大哥请仔细瞧瞧,这都是你往日扔掉的残花。”马子才怔然若痴,不能置信。
少年来到前门,大声道:“今日到此为止,大家明日请早吧。”不理人群抗议,“啪”地关了门,进屋端了酒菜出来,摆在花畦之侧,道:“多日未得与大哥喝酒了,今日需尽兴。”马子才失魂落魄地坐下,手里捏着筷子,眼睛瞧着花圃发直。
这顿饭马子才食不知味,当晚辗转一夜,心中又兴奋,又迷惘。兴奋的是一日之间,见了无数从未见过的妙品;迷惘的是,始终想不通少年是用了什么神妙的手段,竟能化劣为神,点石成金?次日一早听得鸡鸣,赶紧起床,又去看少年的菊花,只见昨天亲眼看见少年新插的一些花枝,竟然也都已经生根萌芽了。
这是逆天悖理,绝无可能的事情!这时少年正端着一笼烧麦出来,马子才再也忍不住,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道:“这究竟是什么奇术,请贤弟教我!”
少年无奈道:“不是小弟藏私,此术无可言传,更不能身教。其实无非奇巧淫技,似是而非,皆是幻象。小弟为了谋生,不得不为之,大哥又不卖花,就学了也没用。”
马子才奇道:“怎的会是幻象?”
少年神秘兮兮道:“明年此时,便可知晓。来来来,先吃早点。”
大约是售罄的缘故,聚在陶宅门前的人,一日少似一日。几天后,少年雇了几辆大车,用蒲席包了菊花,自归金陵而去。到了年后仲春,才满载着南国异卉归来,去北京城里开了间花铺,不到十天,售卖一空,反而引得大批京中豪客追到门上来求购,陶宅又恢复了门庭若市的局面,许多去年的买主,亦赫然在列。马子才悄悄一打听,原来去年买回的花,凋谢之后,再度生发,竟全成了劣种,买主们百思不解,马子才却想起了少年那句“奇巧淫技,皆是幻象”,若有所悟。
少年靠着“奇巧淫技”,积攒下大笔财富,两年之间,几间斗室,变作栉比华居,旧时花畦,尽为廊舍,另外买下大片沃田改成花圃,雇了花农来种。每年秋日载花而去,春尽不归,家中事务,全由黄英料理,售花所得,自拿去与相熟的商贾合股做生意,由是资产益厚。
相形之下,马子才的光景却更加不妙了,马太太宿疾缠身,竟然不治而死。死前将当年与黄英的一席交谈说给丈夫听,当年黄英有“四十三个月后出阁”之言,屈指而算,到如今刚好满四十三个月。
“陶家姊弟必非寻常人物,有黄英在你身边,我也能放心去了……”
马子才含泪送走了太太,忽有一封书信送来,是那少年所寄。打开一看,竟是嘱咐姊姊嫁与马氏续弦。马子才大奇,他远在天南,怎么会知道我妻子故世?即使他们姊弟有信函往来,这封信又怎能来得如此巧法,妻子才去,信便到了?
虽然双方至亲皆有意促成婚姻,黄英亦不反对,但马子才毕竟不能妻子新丧,立结新欢,因而迁延一年后,姻好方成。黄英令人打通隔墙,两家真正合为了一家。
第二年,马子才因事欲往金陵,临行之前问黄英,小舅子栖身何处?黄英推说不知。到得金陵,正值菊秋,料理完事务,马子才花瘾又犯了,一头钻进花市乱逛。这几年他见惯陶氏姊弟调理的各色异种,早把眼界养得极高,寻常品种怎堪入目,因而游赏半日,见十里秋色,尽是庸脂俗粉,不由有些意兴索然。
待要回转客栈,忽听跟班的长随说了一句:“老爷你看,那边倒有许多花。”马子才转眼看去,果然盆列甚繁,款朵佳胜,心中一动,莫不是小舅子的花铺?赶过去一看,少年白衣胜雪,揽一把杭扇,正于那万花丛中倚榭而坐,悠然品茗。
两人相见各自欢喜,少年邀马子才搬了行李过来住下,盘桓数日,马子才记挂娇妻,劝少年同他一道北返。少年却不肯:“当日北上,原为护送家姊,而今姊姊既得归宿,我也就不必再操心了。何况金陵本是故土,我打算在此结婚生子,老死于斯。哦,对了,”说着入内取出几锭黄金,道:“近日积得一点薄资,请交给姊姊。”
马子才不接,道:“家里的资产,足够下半辈子吃穿不尽,你何必还要辛苦营生?至于娶妻,包在我身上,即管让你满意。你姊姊天天念着你,还是跟我回去罢。抱菊!”
一声喊,那个名叫抱菊的长随哈着腰上前应道:“老爷。”
马子才指着那些菊花道:“你帮着舅爷料理料理,把这些花统统卖掉,好接舅爷回家。”
少年无奈,只好由着他们主仆将上百本珍品一概贱价处理,雇舟而北。不一日抵家,黄英已经收拾好了一间屋子,连裀褥衾被一并整理妥帖,供少年起居。
马子才大奇,问道:“娘子,怎的你竟能未卜先知一样?”
黄英淡然笑笑,又不答话,留马子才一个人在那里咨嗟不已,大叹神奇。
少年归来后,听了姊夫的劝,果然不再出去卖花,每天同马子才弹棋喝酒,替他做媒时,却又不要。黄英便买了两个俏婢服侍他,一年两载,耳鬓厮磨,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天,有个姓曾的书生来访马子才,置酒招待,少年打横相陪。曾生酒量如海,马子才不是对手,少年却大喜,两人一杯接一杯,从早上直斗到次日凌晨,各自豪饮不下百壶,曾生终于支持不住,倒在椅子里烂醉如泥。少年拍手大笑,道声“承让”,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出得门去,一跤栽进菊畦。马子才大惊,生怕小舅子摔坏了,忙上前扶时,却见少年衣服散落一旁,身子化成了一株巨大的菊花,比人还高,十几朵碗口大的花颤颤巍巍,傲放枝头。马子才骇极,踉跄奔进卧室,喊醒黄英道:“不得了了!阿舅他……他……变成花了!”
黄英遽然披衣而起,急步赶出,见了那菊花失声道:“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小心地将花连根拔起,平置于地,盖好衣衫,待天亮的时候,重又变回了少年,躺在花丛中呼呼大睡。
马子才惊异无已,黄英道:“事到如今,也不必瞒着相公了。我和舍弟,原是独龙阜上,灵谷寺旁同根连干的两枝野菊,因久得蟠龙灵气、日月精华,万载千秋之下,修成人形。当年妾身心动,欲观北国风光,差舍弟驱车护送,中途遇到相公,感于相公惜花护花,不禁心许。今日舍弟不慎,原形毕露,若惹得相公见恶,可出一纸休书,我二人自回金陵便了。”说着,花容惨淡,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似的凝视着马子才。
“娘子说的什么话!”马子才略略怔了一瞬,立即恢复从容的神色,绽开笑容道:“怪道娘子这等娴静端淑,花容月貌,原来真是花仙!我马某人一介山野匹夫,何德何能,竟得神仙垂青,结成眷侣?娘子不嫌在下才德庸驽便罢了,我怎会嫌恶娘子?这话再也休提。”
黄英大喜,只是人淡如菊,那份喜色惟从眼眸中淡淡流露,不张不扬。马子才心中一片温馨:想来上苍见我爱菊如命,便派了这样一位花仙姑娘与我为妻,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少年酒醒之后,知道身份暴露,而姊夫毫不介意,于是越发放浪形骸。他因马子才酒量有限,对酌不能尽兴,动辄差人招曾生来,两个酒鬼日日长鲸豪饮。一次,曾生嫌酒味寡淡,饮之无趣,命两个小厮抬出一探药酒,说经秘法酿就,酒力必寻常烈酒更强十倍。少年听得眼睛发光,忙拍开封泥,你一碗我一碗,须臾喝完。两人咂咂嘴巴,兴犹未尽,又往坛子中倒入一瓶白干,涮涮坛子底儿,匀着喝了。没想到那药酒酒力乃是后发,曾生才喝干一碗,咣当倒在几上,醉死过去,两个小厮忙左右架着,半拖半背地负着去了。少年跟在后面大笑:“曾兄!你又输了!”一句话说完,“啪叽”摔倒,变成了菊花。

马子才在旁边看着,不慌不忙,想起黄英的手法,如法炮制,把那菊花连根拔起,平放地上,盖好了衣衫,拖过条凳子坐着,想瞧瞧菊花究竟是怎么变成人的。
等了半天,菊花迟迟不变,而叶子竟有枯萎迹象,这一下慌了手脚,忙奔到内室喊道:“娘子!娘子!快去看看,阿舅的菊花怎么枯萎了!”
黄英脸色大变,疾步奔进院子,揭开衣衫,那菊花根株已枯,她仿佛被雷劈中了似的,蹲在那里,手捧着兀自怒放的花朵,一动不动。
“娘子?”
声音入耳,黄英全身颤抖,剪裁合身的绸夹袄下,肩胛骨高高耸起,入目惊心。马子才心中忽然一片冰凉,绕到黄英身前一看,妻子泪水簌簌落下,大哭道:“我弟弟死了!”
马子才目瞪口呆,手脚一齐麻了,呆呆地望着黄英流着泪掐下一茎花枝,埋进花盆,一语不发地捧着,径自转回卧房。
晚风淅淅,花叶微拂,太阳落山了,少年没有出现,那株巨大的菊花静静躺在泥土里,丝丝冷香,缭绕着寂然肃立的守墓人。
转眼一年过去,飒飒西风,又逢菊季,墙外花圃早已荒芜,昔日万般锦绣,而今惟剩一枝。
窗棂前,花盆中,一朵粉色的小花微微绽放,细嗅有酒香,灌溉以酒,则蔓蔓日茂。此菊天下无双,世人奇之,因取名「醉陶」。
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