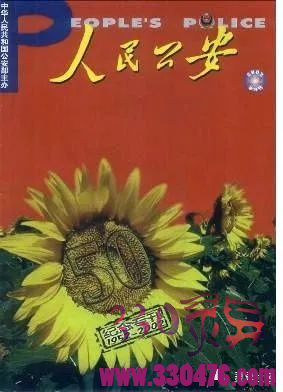过去,东城外有个叫秀山的村子,村中居民多是来自各地的流民,有的人还能记得祖籍在哪,有人因为自幼离家,早已不知自己是何方人士。
那年月战乱四起,灾荒遍地,每天都有人拖家带口进来,也有人拖家带口地走,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活,有的人为了活着,就开始做了买卖。
何兴就是如此。何兴是皖南人士,老家遭了兵祸,不得不带着全家人逃难,不想一路上,八口人的家庭,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与年迈的父亲何德光。他早已是了无生趣,愿追随妻儿入黄泉,只是老父尚在,不得不勉强活着。
那日,他们来到秀山村,见村后有间破草棚,似无人居住,于是进去查看。棚子里杂乱无章,只有一具尸体,不知死去几时了。二人告了罪,将尸体埋在屋后,乞求死者的恕罪,便将草棚收拾一番住了下来。
何德光年老体迈,住下后便大病一场,正当何兴为他准备后事时,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可能是因他经历了生死,便变得沉默寡言了,时间一久,何兴也就习惯了。
二人虽是侥幸有了落脚之地,却无田无地,整日饿得手脚发软。突然一日,何德光不知从哪捡了把生锈的篾刀,磨利之后,又去村后的山上拖下一根竹子来,剖开分出细篾,编了只竹篓出来。他的手法虽然生疏,但编的成品却也有模有样。
何兴瞠目结舌之余又大喜过望,父亲竟有这手艺,那自然是不愁生存了。
何德光的技法越发娴熟,不仅是竹篓,连竹篮筛子、簸箕等只要是竹编的东西都会做,砍、锯、切、剖、拉等等行活令人眼花缭乱,竟半点不亚于做了数十年的老匠人。
何兴看得稀奇,询问道:“爹,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手艺的,我怎半点也不知?”也是呀,若是有这等手艺,过去父亲又何必种田为生呢?何德光只是笑笑,也不说话。这样,父亲在家编竹,何兴拿去市场,一晃三年,父子二人不仅活了下来,还攒了些积蓄。
这日,村里的媒人三婆来了,说是替何兴介绍一个妻子。那女子丈夫去世,无法立足,愿改嫁于他。此时何兴已经年过四旬,而那女人还不足二十岁,自然乐意之极。于是翻了历书,见十五日后,也就是下月初八宜嫁娶,就定在了那日。
当天夜里,何兴照旧随着父亲学艺。他没有父亲的天赋,也过了学艺的年龄,学了三年多,连竹篾也剖不平整。按理来说,今夜也还是练剖篾,但何德光却让他随自己学编织了。日常见得多了,这编的程序对何兴来说倒不是很难,很快,他就学得有模有样了。只是,第二天拿去卖,他编的和父亲编的放在一起,他的却是最后才卖出去。
一转眼间,到了成亲那天了。新人拜了堂,入了洞房,不想何德光却将何兴叫走了。何兴随父亲来到屋后那座无名氏的坟前,不由得诧异不已。他正要询问,何德光开口了,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开口,声音显得很是沉闷干涩,他说:“你不是好奇我为何突然会篾匠手艺了吗?这全是因为墓中之人。”他说,三年前他们在草棚住下的当天,那死去之人便来找他,要与他谈个交易。
何兴听得毛骨悚然,问:“什么交易?”何德光说:“他说他叫李旺,梁州三里庄人,篾匠,遇灾荒而家人失散,逃到秀山后,见这里有无主草棚,便住了下来,不想却得了疾病,死了。他说,他会让你学会篾匠手艺,于乱世之中得一生存之技,但你也得答应,得空时去他家里走一趟,他妻儿若没回来也就罢了,若回了,便通知他们回来过来收敛骸骨,埋回故土。”
何兴瞠目结舌,半天才说:“爹,你平日怎么没跟我提过,今日又为何要说起?”何德光没说话,却逼着他答应了那李旺的要求,这才微微一笑,说:“因为三年前我便已经死了,只因担心你,一口气顶在喉咙里,不生不死,我若说话,那口气走了,也就彻底死了。如今,你有了手艺,还有了家,我也该走了。”
说着话,他毫无征兆地向前扑倒。何兴大惊,上前扶起他,却见他已没了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