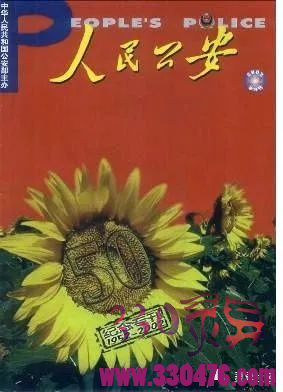小编不知,你遇到过啥样的泼妇,泼到啥程度,但这个故事里要说的大扫帚,保准儿你没见过。不信?接着往下瞧。
大扫帚,是个绰号,家中七里堡,姓唐,大脸盘,大嘴巴,粗腰身。平时,只要和左邻右舍起了纷争,你就听吧,她上下嘴唇一碰,对方的祖宗八代便全倒了血霉。若和她对吵的是老爷们,她不光骂得花花,还会抄扫帚,劈头盖脸开抡。
由此,绰号来了:大扫帚。有一回,忘了为啥,大扫帚和邻家男人呛呛上了。骂不过瘾,扫帚又被夺,她索性当着一众老少爷们的面,扯了衣裳,脱了裤子,就地打起滚来:来人啊,救命啊,大柱子那个啥我了——
那个啥,很粗俗,不好说出口。从此,大扫帚名震七里堡。沾不得便宜,便脱裤,污你。当然,和外人吵,终归是少数,她动不动就抡大扫帚拍的,是公爹老蒋头。正如这日,老蒋头的儿子蒋呲牙外出打工,扛起铺盖卷儿前脚刚走,大扫帚便冲老蒋头瞪了眼:
“老东西,老不死的,还不滚回窝棚去?谁家老人像你似的,整天啥活不干,就知道吃喝睡!”
老蒋头身子有病,干巴瘦,劳碌了一辈子,也快耗干了心力。见儿媳大扫帚嗓门越来越高,忙说:“家和万事兴呢。你小点声,别叫人听见,”
“干啥鸟悄的?呲牙娘死的早,你想扒灰啊?”大扫帚手一捞,就抓起了大扫帚。
老蒋头慌张取了锅,往外走。天已冷,住地里的窝棚,没米没面,没油没盐,烧一锅热水喝也行啊。哪料,一扫帚打来,咣当,铁锅落地;老蒋头没敢捡,顷刻浊泪横涌。
故事说到这儿,有必要提一嘴老蒋头的窝囊儿子蒋呲牙。当大扫帚撒泼时,蒋呲牙并未走远。街邻便劝,道:“呲牙,你媳妇骂你爹呢,也忒不孝顺了。”蒋呲牙嗫嚅半晌,总算挤出了个屁:“要你管?!”
得,遭狗咬了。有时,街坊邻居也扎堆,嘀咕,大扫帚为啥那么泼,忤逆不孝?合计来合计去,讲真,还真没人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天性吧。老娘就这么泼。不服?放马过来,老娘脱给你看!
闲话少叙。且说这年腊月,老蒋头殁了,随黑白无常进了鬼门关。走时,两眼瞪得圆圆的,鼓鼓的,白事先生揉按了半天,也没能给他合上。没辙,往干巴成山核桃的脸上蒙块布条,就那样入了棺,下了葬。听说,老蒋头的肚子饿得瘪瘪的,该有几日,粒米未进。
蒋呲牙得到丧信儿,忙忙赶回。邻家男人忿忿:你媳妇,就欠揍。蒋呲牙一咬牙,抓起半截砖头要去教训大扫帚。哪料一照面,大扫帚就抡圆大扫帚,将他打靠了墙:“王八蛋,胆肥了你。今晚,不,这半月,你甭想上炕!”
啪,蒋呲牙将板砖拍上了自己的脑门,哇哇大哭:“爹,儿子得有媳妇,得给你生个大孙子,把咱蒋家的香火传下去啊——”
其实,老蒋头去世,大扫帚心里也怕,也胆突。做了亏心事,哪能不怕鬼敲门?在老蒋头入土的次日,大扫帚就揣着一沓子钱,去了狗市,买回两大一小三条每一根杂毛的黑狗。院门口和屋门口,各拴一只大的,晚上睡觉,搂着只狗崽。据传,黑狗是鬼魂克星,甭管厉鬼凶鬼饿死鬼,皆怕它。此外,还请了数尊门神,驻宅驱邪。
这回,该万无一失了吧?不,还是出事了——
就在老蒋头烧头七那晚,吱呀呀,院门忽悠悠地就开了。大扫帚以为是蒋呲牙,张口就骂:“呲牙,你不关门,怕夹着你那狗尾巴啊?”
没人回声,黑狗也没叫,就那么慵懒地趴在地上,歪着头,冷着眼,瞅她。大扫帚抬头瞧看,登时妈呀一声叫,吓白了她那张葵花大脸。
来的,不光是公爹老蒋头,还有早死多年的婆婆,就那样直勾勾,阴恻恻地盯着她!
你打骂、欺负人家的老头子,人家自然要来找你算账。而门神,黑狗,竟然全都鸟悄的没发出半点声响。
“你、你们来干啥?”不待大扫帚躲闪,婆婆已探手掐住了她的脖子,直掐得她白眼直翻:“泼妇,要你命!”
不过,大扫帚没死。最终,老蒋头又动了恻隐之心,重重叹口气,拽走了老伴儿。但有一点,确是事实:
大扫帚突然间就疯了。不论冬夏,冷热,如她当街撒泼一般,常脱得一丝儿不挂,手里拽着只大扫帚,到处疯跑。蒋呲牙则拎着被单,屁颠屁颠地追:“媳妇,求你穿上衣裳啊,咱可不能光屁股跑,转圈丟人啊!”
至于大扫帚为啥会发疯,从她又哭又笑的疯言疯语中,大伙儿猜测、加工出了以上婆婆寻仇的版本。但个中真相,从此成谜,无人得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便是:
孝为人之本。人若大逆不道,你瞧吧,连门神都不保你,黑狗都冷眼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