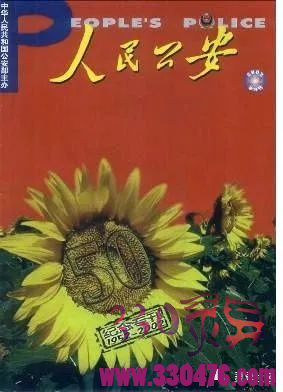多年前,在六方屯东头的野地里,搭着一间窝棚。窝棚破败透风,住着一个老者,年逾七旬,病歪歪干巴瘦,姓丁,人唤老丁头。且说这天晌午,大雨来得急,“哗”的就浇了下来。
外面大下,里面紧漏,滴滴哒哒成了流,老丁头暗叹口气,倒腾出破饭锅破饭碗,摆了一地接雨水。这厢正忙着呢,雨空里骤然滚过一个炸雷,呱啦,直震得老丁头两耳嗡嗡响,差点聋掉。
说来也怪,雷过,雨停,眨眼功夫,天儿晴了。老丁头挪出窝棚四下一瞧,顿觉心头一咯噔。
六方屯毗邻深山老林,随处可见参天老树。而就在数十丈远处,一棵歪脖老松树下,恍惚趴着一个人。老丁头顾不上多想,侧侧歪歪就奔了过去。
是个年轻村姑,眉目俏丽,当是遭了雷击,昏迷不醒,好在尚有一丝余息。老丁头紧忙弯腰,抱起她回了窝棚。
掐人中,按虎口,喂水,老丁头忙到天黑,又一眼不眨,守了个通宵。天亮时分,村姑总算悠悠醒转,说她叫白篱,是外乡人,昨儿个从六方屯走,不幸被雷震晕。“老伯,这是哪儿?”
“这是,是,”老丁头欲言又止,似难出口。
“你一个人住?没儿女?”白篱又问。
不等老丁头答话,便听一阵阴阳怪气的动静钻进了窝棚:“你谁啊?瞎打听啥?咦,长得挺俊的。你叫啥?嫁人没?”
随着怪动静进来的,是个鼠目蒜鼻歪嘴巴的矬汉,盯着白篱一个劲地嘿嘿笑。那眼神,直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心发毛!
这个矬汉子,叫丁二三,是老丁头的独子。想当初,老丁头中年得子,乐够呛,还想开枝散叶多要几个,便给其起名丁二三,接二连三嘛。岂料,就这一个,就让老丁头操碎了心。小时,上房揭瓦,偷鸡摸狗,专干缺德事儿,生生把娘给气出一场大病,殁了。老丁头恨铁不成钢,也没少抡棍子揍他。可白扯,丁二三属狗的,记吃不记打。及至长大,丁二三愈发胡闹,混账,吃喝嫖赌,还记了父子仇,把老丁头给轰出了门:
挣钱去,啥时给我说上媳妇,啥时回来!
老丁头老了,又一身病,干不动活,无奈,只好住进了地里的窝棚。即便如此,丁二三隔三差五就来闹腾。这不,又让白篱给赶上了。
“妹子,来,我给你讲讲做人的道理。”丁二三连推带搡,将老丁头撵出窝棚后,一屁股坐在了破床边,“这在世为人啊,要讲良心,要知恩图报。你看,你是我家那老东西,不,我爹救的,这恩情,可比山重啊。”
“你啥意思?”白篱问。
丁二三觍脸讪笑:“你得报恩,嘿嘿,嫁给我当媳妇呗。”
白篱想走,可身子痛得紧,坐都坐不起来。眼见丁二三趁人之危,动手动脚,便道:“我已有夫家。要不,等我好了,我把堂妹嫁给你?她叫白秀,白白净净,很秀气,只可怜父母早亡,孤苦伶仃,还是个哑巴。”
“哑巴好啊,不磨叽,不烦人。”丁二三大喜道,“我这就去偷只鸡,给你炖汤喝!”
“别急,我有个条件。”白篱说。
“只要能娶上媳妇,嘿嘿,别说一个,一百个我都应你!”
白篱的要求,有些古怪:把老丁头接回家,好生伺候,安享晚年。若再忤逆,她就把堂妹接走。丁二三听言,当即拍胸脯子发毒誓,并背老丁头回了家。白篱也没食言,及至伤愈,还真领来了哑堂妹白秀。
果真是白净,秀气,老老实实,稀罕死个人儿了。丁二三一见,就直了眼,淌了哈喇子。
长话短说。一转眼,半年过去。老丁头活了一辈子,好歹享了几天福,吃了几顿饱饭,丁二三还给他洗过几回脚。用他的话说,这辈子,知足了。哪料,日子一长,丁二三便烦了,故态复萌,而老丁头也寿限将近,病倒了。
坏了,老家伙要去了阴曹地府,白篱指定来接白秀。我和黑白无常也非亲戚,人家不会尿我,放过老家伙啊。这可咋整?踅摸来踅摸去,丁二三一咬牙,起了狠念。
爹死,挖俩坑;然后磨刀,白篱要敢来,就弄死她,一块儿埋了!
话说这日,老丁头闭了眼,魂归黄泉。为防万一,丁二三捆了白秀的手脚,藏进了小黑屋。接下来,给老爹发丧,下葬,忙忙活活烧完头七,却始终没见白篱露面。
“媳妇,你堂姐要来,我可不惯着她。”这晚,丁二三喝大了,摇摇晃晃钻进了小黑屋,“媳妇,这几日,光顾着发送老家伙了,没好好疼你。嘿嘿,我这就给你解绳子,抱你回大屋,上炕。”
探手一搂,丁二三便把白秀抱了起来。
咦,咋飘轻呢,该不会是饿瘦了吧?丁二三晃晃脑袋一瞅,登时妈呀一声惊叫,哗哗尿了裤子。
天呐,抱进怀里的,竟是个白森森的纸人儿!
这桩诡事儿,当夜便传遍了六方屯。有人说,那白篱,其实是只千年白狐,渡劫遭了雷击,幸获老丁头搭救。她的堂妹白秀,是出自扎作行的纸人。白篱使了小法术,让它活了,做了丁二三的媳妇,也为老丁头换来了几天福气,减了几分遗憾。
奶奶的,这半年多,我睡的居然是个冥纸人,纸媳妇。不光瘆人,还吓人,吓死人。丁二三忿忿叫骂:“你个活该雷劈的狐狸精,竟敢耍我,糊弄人!”
糊弄人?忤逆不道,吃喝嫖赌,乘人之危,你算个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