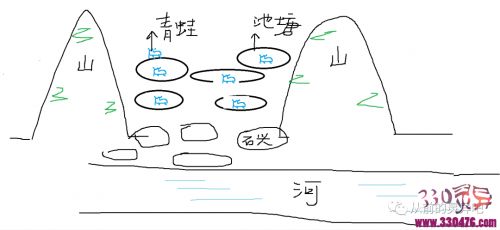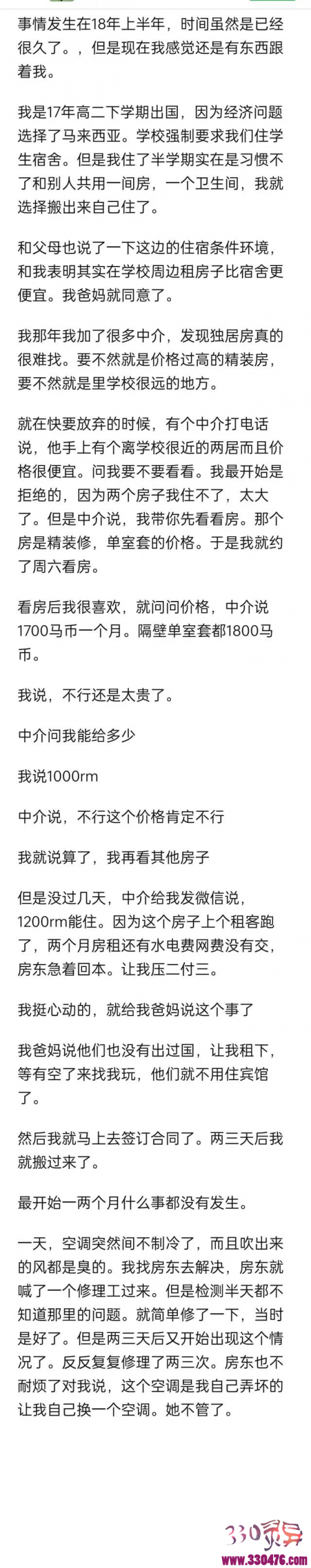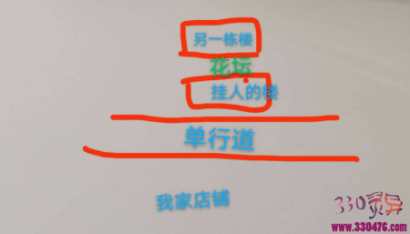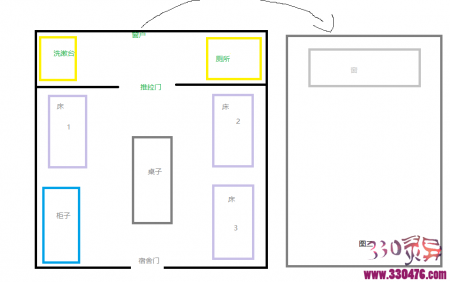春暖花开,又到了去游乐园的季节。游乐园里长盛不衰大排长龙的项目,除了过山车,非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莫属。看着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前拐了好几道弯的队伍,我不禁陷入深深的疑惑之中:花钱寻开心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被吓?

现在有各种主题的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体验,中式的、欧式的、日式的……|pixabay
为了给看完恐怖片都要开灯睡觉的自己一个交代,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四月天,我伙同绵绵、路西、Edan三位同事,勇闯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
尖叫
不忘社畜的本分,为了能去完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后继续回来工作,我就近选了一家位于北京CBD某商场内的美式恐怖体验馆。
由于到达时前一拨人刚进去,我们在西式装潢的等待区等了近二十分钟。聊天的话题从考古现场挖出来的结石,到尸体上的蛆,再到肝肠胃等人体器官的触感,不一而足。在和同事交替去了厕所后,我悲伤地发现:面对未知的恐惧,专业素养好像派不上什么用场——不管是操刀解剖过尸体的绵绵,还是与遗骸亲密接触过的Edan,或者是身藏健壮腹肌的路西。
还是害怕。

不确定性是加剧恐惧的原因之一 | pixabay
被自己的想象吓得打了几次退堂鼓后,我们签名保证身体健康,检票入场。经过完全黑暗的一节通道,我们被请进一间有着大长餐桌的房间,桌上有花、瓷盘、金属餐具和餐罩,好像是在参加吸血鬼的晚宴。房间里回荡着小女孩哼鸣般的呜呜声,而这个背景音将伴随游戏全程。
这时候一个穿着T恤的工作人员开始讲解注意事项,要点是一定不能殴打、谩骂扮鬼的员工(NPC)。工作人员表示,大家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自然反应啊,否则会被终止游戏的。
这一点,很重要。
在进入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个软妹,从来没有打过人骂过人,碰到鬼只有吓到嘤嘤嘤的份,能有什么过分的“自然反应”?

专业NPC不会随便放过你的|pixabay
首先是尖叫,我从没想过尖叫可以如此自然。第一关入口处是第一个NPC亮相的地方,也许是规定动作,这位带着白色面具的鬼要与一组六位游客中的每人近距离接触。作为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NPC,他不会因为你大叫“走开”、“别拉我”就真的放弃工作。这位NPC在每个人脸上闻了一圈后,抓着我的脚把我从椅子拖到了地上——我没想到他真的会用力拽啊,有谁生活里被拖在地上过啊!我大声尖叫。
之后,第一关正式开始。
哪里都黑黢黢的,就像是晚上没开灯的房间,到处是布帘子、布偶、镜子、空桌空床之类的恐怖元素。我还在观察环境,耳旁就传来Edan的尖叫声。NPC把虫子(对人体无害)放在了她的膝盖上。
一个房间一关。关卡房间布置成育婴房、教室、浴室、屠宰场等恐怖主题,路线迂回,在行走时需要不断拨开前方布帘之类的遮挡物。恐惧让人想要快速通关,但快速通关意味着会更快遇到吓你的NPC。在这个矛盾中,我们战战兢兢跟随着前面的游客移动,一边全力观察房间里每一个细节。

到处是布帘子、布偶、镜子、空桌空床之类的恐怖元素|pixabay
突然,从侧面冒出来一个NPC。
“啊啊啊————”
四人的尖叫声混成一团,不分彼此。
作为人类生存演化的工具之一,尖叫在吓跑掠夺者的同时,也在提醒他人注意附近的危险。多伦多大学的学者亚当·安德森发现,人们做出恐惧的表情时,视野范围更大,眼球运动速度加快,鼻子的呼吸频率增加,嗅觉更加敏锐。
无论是短促的尖叫还是长长的哀嚎,都是在压力状态下的本能反应,但这种行为不被社会所接受,除了在特定的环境中。社会学家玛吉·克尔认为,对于每天克制尖叫的人来说,真正的放松就像是一种宣泄。控制自己不去做某件事情带来的焦虑、耗费的专注力令人筋疲力尽。你可以回想一下,在完没了的扯皮会议上,为了保持礼貌的微笑自己做出了多少努力。
刺激的活动为控制内心冲动的“警察”提供了休息场所,让“警察”能够小憩片刻。而我们,能够尽情宣泄。
享受当下的恐惧
为了研究恐惧,玛吉·克尔不但常驻美国最知名的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之一“ScareHouse”,还会拉着刚从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出来的体验者做脑电图。玛吉发现,侦查到危险的信号后,我们的身体会进入高唤醒状态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威胁。一连串让人感觉良好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会被释放,如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等等。我们之所以不喜欢火灾、车祸、医疗事故等情境所触发的恐惧感,不是因为我们厌恶恐惧给身体带来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生存,而非享受恐惧。

危险将触发高唤醒状态|pixabay
而对于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过山车等项目,我们在体验之前,就明确地知道,这是安全的。即便在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里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开,我们心里还是有底的:“都是假的!”、“赶紧走完,就解脱了!”于是,我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恐惧带来的高唤醒状态中。
在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里,虽然从侧面冒出一个穿着白衣带着面具的NPC很惊悚,但和NPC一同出现在视野里的往往还有铁丝网、栅栏之类的隔离。这像是游客心理上的安全网——虽然我被吓了一跳,但我知道他不能隔着网把我怎么样。
这也像是对NPC工作人员的防护网,因为在人感受到威胁时,几乎会本能地用肢体反抗。练舞四年的路西,就在情绪的作用下,踢了栅栏一脚。当然,她真正想防范的是躲在栅栏后面用单调骇人的节奏一下一下敲击栏杆的NPC。

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差不多就这个亮度|pixabay
执行工作人员关于控制肢体行为的嘱托,对大脑内存告急的我们来说并不那么容易。
除了不要过于激动外,进入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之前工作人员还特别指出来,如果过于害怕要退出,可以抬头找红点,向摄像头示意。我当时很想问,如果我找不到摄像头怎么办?可以跟NPC要求退出吗?如果我跟鬼摆手,鬼会带我出去还是会卯足了劲吓我?
进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之后,我就没闲心思挂念红点了。虽然NPC经常在前面等你,但是,在所有关卡走过之前,你总会对这个黑暗狭小的房间有无数恐怖的想象。比如,这个课桌下面会不会伸出一只手拉你的脚?躺在水池里的假人是不是真的假人?会不会突然跳起来?这个镜子后面是不是有人?不对,好像上面带血……

应对威胁时,负责理性和逻辑的脑区将不再主导|pixabay
“啊啊啊————”
又是一阵尖叫。
范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扎尔德发现,当我们因为被吓处于高唤醒状态时,为了确保机体有足够的能量以达到应对威胁的目的,不必要的系统会被关闭。负责理性和逻辑决策的前额皮层,会让位给大脑中负责更低级、更原始功能的部分。我们全心全意应对威胁,暂时忘记了昨天和朋友的争执或是明天的信用卡账单。
用一句俗话说,我们活在当下。
重回光明
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关卡的路线很窄,只允许一个人通行。我们四个人夹在队伍中间,两两前后拉紧双手,时不时还紧紧抱在一起。你搂着我的腰,我挽着你的肩。
不得不说,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冒险是非常好的破冰方式。如果你有喜欢的暧昧对象,来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也许能增进感情。如果双方感觉不那么对就算了,你可能会经受来自尴尬与恐惧的双重考验。
游戏设计时间是三十分钟,我根本不知道通关用了多久,我没有看表,像是十几分钟。推开最后一关的门,房间被红色灯光映满,一架转动的电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所有人在这一刻跑向出口的大门,在商场的冷光灯下放声大笑。

出来时还是挺快乐的|pixabay
好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又像是终于回到了一个有掌控感的世界。
在外头等待的同事雪竹说,她先是听到了一阵清脆欢快的笑声,还以为是来了一群边逛街边嬉闹的学生。没想到是刚从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里出来的我们。据她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满脸通红,眼睛放光,嘴角快咧到耳朵了。
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参与刺激体验,我们不是简单地得到快感,而是重新校准了抗压能力——当我们把自己逼到极限,过去那些每天困扰我们的事情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连鬼我都不怕,还怕人吗?
虽然鬼是假的,但战胜困难的体验是真的。虽然是在安全有保障的框架中体验刺激,但在连续不断的尖叫中体现的韧性、自信和突破,即使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也是真真切切的。还让人感觉很不错。
在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体验的几天后,我们再次回想当时的经历,发现心里没有一丝恐惧的阴影。这与恐怖片的细思恐极非常不同。
我们把尖叫声和手心里的汗都留给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

鬼是假的,但战胜困难的体验是真的|pixabay
我们不但不害怕,甚至还觉得不太过瘾,开始给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提意见:“这里应该放个NPC拉我的脚”,“那里应该把鬼放出来追着我们跑”。最后,我们得出了统一的结论:美国风的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有文化差异,不利于我们全身心地投入。
于是,我打开点评APP,标记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一家日系恐怖风、运用AR技术的世界上最恐怖的鬼屋。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