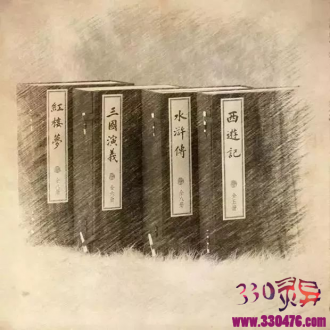曾经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会背诵《情人》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开篇被王小波称作“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上世纪90年代,杜拉斯在中国风靡一时,虹影说:“中国女作家都受过杜拉斯的影响”,远的如林白、陈染,近的如棉棉、卫慧、安妮宝贝,观念与创作无不受其强大辐射。
杜拉斯甚至一度诡异地融入中国小资文化的潮流,喝星巴克,读杜拉斯,是当时都会女郎好品位的象征。而真实的杜拉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作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以晦涩迷离而著称。
她极端而鲜明的个性,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注定对她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爱恨交织。就像有评论所说,她的读者也是“被选择的”,喜欢的人被她层出不穷的警句一语击中,从此欲罢不能,不喜欢的则似一头雾水,无缘靠近。


1935年,杜拉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法学院。日后她总结自己这段生活:那时候过着“一种骚动的生活”,浪漫史不断,近乎放荡。“如果不当作家,我就去当妓女。”她曾说过如此惊世骇俗的话。
1938年毕业后,杜拉斯进入法国殖民部工作,在国际信息资料部当助理。期间,她和自己的上司一起合作写了一本《法兰西帝国》,在书中赞美法国的军队和殖民主义,为法国的殖民政策背书。
杜拉斯后来从不提及这本书,大概是把它当做自己年轻时犯的“错误”。1939年,战争迫在眉睫,杜拉斯给已入伍的恋人罗伯特发了一封求婚的电报,请他速回。


她非常欣赏罗伯特的学识和智慧,很听他的话,这大概在她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1939年9月23日,两人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婚礼。夫妻俩保持着一种松散自由的关系,两人各有情人,互不干涉。
杜拉斯曾在战时的出版检查分配处做秘书,初审书稿,她总为爱情故事开绿灯。她对审读员马斯科罗一见钟情,因为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她疯狂爱上了他,和所有的情人断绝了关系。
她把马斯科罗介绍给罗伯特,两个男人出乎意料地一见如故,成功建立起一种乌托邦式的三人世界。马斯科罗后来成为她唯一孩子的父亲。二战时三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出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是他们的战友。


密特朗多年后回忆:“我们当时唯一的激情,都倾注到了对真理的追寻上。”圣伯努瓦街5号,杜拉斯的家,变成了自由友谊之舟,为抵抗组织的志士们提供藏身栖息之所。
杜拉斯也懂得如何招待客人,做得一手好菜,美妙的熟肉点心和越南米饭,知道在哪儿能买到巴黎最好的猪尾巴。她在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传递信件,组织成员碰面,密特朗称赞她是一位投入满腔热情的出色联系人。
1944年,杜拉斯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把它看作是她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历练,“非常无情,由于它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迫使你作出的不断修正”。圣伯努瓦街5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


40年代末,杜拉斯对法共内越来越明显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不满,参加党内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也因为她猛烈的公开批评,以及“个人生活腐化”,1950年收到她的退党信后,法共正式将她开除出党。
“灵魂深处我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今后还能做什么样的人。”
杜拉斯与波伏娃两人互相瞧不上,两人曾拥有一个共同的情人博斯特。杜拉斯说:“波伏娃一钱不值”,波伏娃则说:“解释一下,我可看不懂她都写了些什么”。


杜拉斯想在萨特主持的《现代》上发表文章,被他粗暴地拒绝了,“您写得很糟糕,不过这话不是我说的。”
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杜拉斯选择与萨特、波伏娃一起并肩战斗,从一般的表态到公开站到法国政府的对立面,她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54岁的杜拉斯参加游行,奔跑在警察前面高呼口号,跟着大学生占领巴黎索邦大学,不分昼夜听学生演说。当时著名的运动口号,“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但这不能成为不走的理由”,“禁止一切禁止”等,都出自她的手笔。


杜拉斯热衷搞政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搞政治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搞政治更幸福、更令人心醉神迷的事情了。”她喜欢大放厥词,谩骂或诅咒,也无视所谓的“政治正确”,极端一如她的文学:
“让世界走向消亡吧,这是唯一的政治”,“我不赞成拥有妻子和孩子,今天的年轻人们已从这种优先考虑占有的爱情模式中摆脱出来”等等。往往左派不喜欢,右派也不接受。不过她也不在乎,依然一如既往。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他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1917年1月5日-1990年10月26日)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弟弟和朋友。
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1916年-1990年8月20日),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

杜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情人》剧照
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直到她70岁时,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成为了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
她一生拥有众多情人、经历了各种感情的纠葛;她的作品无论用何种方式写成,都离不开爱情这个深刻的主题。而更关键的是,她的16岁初恋献给了钱;而她一生最后的恋人,在外人看来就是被包养的男子。

杜拉斯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情人》海报
“爱的是钱还是人?”在她的故事里,谁又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爱要么就是一切,要么就什么都不是!